深冬,寒风剌面,透骨凉。
公交车上,人人都用皮大衣羽绒服裹得严严的缩作一团,只露俩窥物的黑眼珠和换气的红鼻孔,不时喷出两道粗壮的白气,四下散开。接着又是第二道,第三道……
车停了,上来一位胡子花白,身着一套老式绿色军装的老人,胡子上还揸着冰渣,右手紧紧往回收着,很显然——这只是一件装饰品。
可是,车上已没有座位了,售票员也无所表示,老人只好用仅剩的一只左手费力地抓住车顶蓬上的扶手,身子随着汽车颠簸而前后摇晃。
而乘客们却对此视而不见,都懒洋洋地闭着眼打盹,也不管车子有没有到达自己所要下车的站口。
售票员熟视无睹。
“大爷,您过来坐这吧。”一声叫唤唤醒了打盹的人们,也引来了他们惊奇的目光。
寻声望去,只见前排座位上一位十六七岁学生模样的女孩站起来招呼老人。
此时,随着汽车的颠簸而前后摇晃的人成了女孩。
老人坐下后不久,便弯腰去系那一双旧式军用运动鞋鞋带,任凭他一只手怎么摆弄,鞋带始终系不上。
乘客们仍然眯着眼睛打盹,售票员也仍然看不见。
“我帮您。”
睁开眼,看到小女孩正蹲在老人面前给老人系鞋带……
乘客们稍稍放松了些,不再裹得那么严实了,偶尔还有一些骚动。
到站了,小女孩下车了,像一朵鲜花,更像一阵风。
然而,车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景象,人人都用皮大衣羽绒服裹得严严的缩作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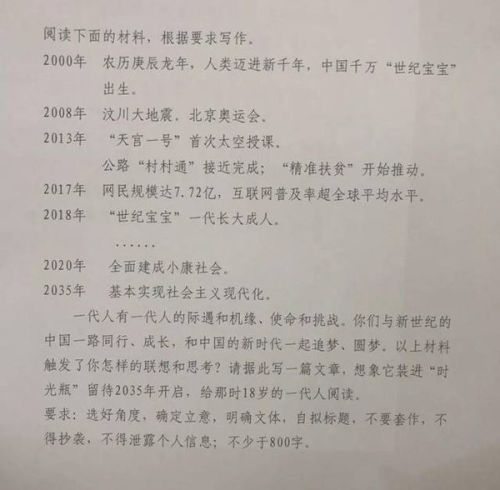
 柳爱常
柳爱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