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没想过自己何时悄悄垒成了躯壳,偷偷将自己藏在黑暗深处,当自己猛然发现早以被壁垒层层包围,想挣脱,却早已经觉得无济于事,思索那一阵阵呐喊声,抬起头隐约发现四颗脑袋搭在壁垒边缘,大大小小,自己宛如井底之蛙,好奇的探头,开始伸展自己蜷缩着的四肢,试图伸手,不经意间有一双手抓住了我那悬在半空恍恍惚惚的手,那一刻抓的更紧,离垒口更近了。
多了几双手,多了几个人,多了几分慰藉,几双手握得更紧,还好那一时刻,某一分,某一秒,有那几个搭拉着的脑袋。壁垒,还是壁垒,永远都逃不掉。几个人探着头,接触着那几个人,时间漫长,壁垒下的人还会认为自己是那井底之蛙吗?我们长大了,隔开着的壁垒,分走了几个人,永远隔不进那几个人,欢声笑语的人,笑声淡了,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只不过是在壁垒下压抑着的借口,找到了借口,却永远找不到出口。
过了多少年,多少个世纪,小四楼变成了公寓,好多大学生,好多人,挤破了脑袋想住在公寓40坪的所谓的两室一厅的房,挤着狭窄的空间,丢掉了家里的小四楼。城市繁华,城市奢靡,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冲动让我们得到一切,错误的思想,构建了一层层壁垒,让我们迷失在层层的躯壳之下,望着以前的纯朴,想起现在的为己谋私,谁都发现了自己变了,谁都不敢承认自己变了。层层躯壳,奢靡极至,蜗居在40坪狭隘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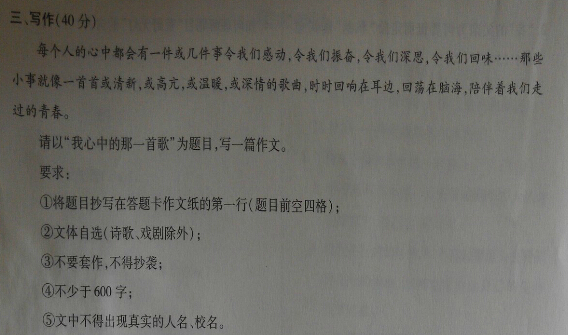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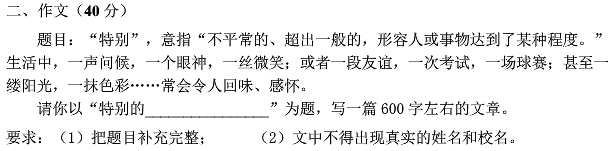
 FuckYou18035326
FuckYou1803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