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朦朦胧胧如丝如毛,深深叹吸进几许湿润了肺,弄花了眼,原本如雾的世界被珠泪的光照得更加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犹如仙界,神圣不可侵犯。
那可是故乡啊!
我就一直杵在村口,雨也一直地下。我似乎赌气似的:雨不停,我就不进去。好像老天爷也怕了我这个倔强的老兵,赶紧停住雨拉开帷幕让我过。我胜利的苦笑几声,末了还拿铜镜照照,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毁了我那“英俊”的形象。不错,还挺帅的!――我苦笑几声。
父母不知安否?还会记得我吗?是否会接受如今的我?
春风抽丝柳条扬。草色青青接碧天。这美景何时才能休止,因为景色越美,我就愁肠百转,泪眼凄迷。十五岁那年,也是在此地,也是这等模样,我被紧急强征参军在此地告别。六十五年后,我回来了。可是六十五年的军旅生活使我再也不是原来的我,脸上有条狰狞的疤,加上六十五年的杀戳带来的杀气使我更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还会接受我么?
慢慢地走着,步履蹒跚非已老,只是有种莫明的恐惧、害怕。
可能是我杀气未消,又或是慑于我脸上的疤,路上的行人竟纷纷避我。这让我更加担心!兄弟死了,恋人走了,人老了,军队不肯要我了,我怕连父母也嫌弃我。如果,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该走了。
我家地处偏僻,虽进了村,可还得穿过一个山冈。在冈顶,不知何时建了一个亭。从碑文得知,有对老夫妇在儿子随军出征后,日夜思念,便到此守望,不分日夜,无论风雨,最终积疾,逝。临死前建了那个亭,希望在他们死后能代守望儿子归来,多美丽的故事啊!
凭着记忆,摸回了家。
等等,这是哪?
斜阳西倾,在勉强能称为房屋的房屋上,像落日砸孤屋似的,使屋顶破了个大洞,好像连老天爷也要跟它过不去。漫天红霞血满天,谁能言尽苦与屈。风声低低,死气沉沉,野兔穿洞,山鸡绕梁,鸟悲鸣,杂草丛生,荒冢累累,谁能与我言。
难道是我走错了?不会啊,梦里无数次的重返,怎么会错呢!
死了?死了?难道是都死了。
哦!死了就死了吧!
我真是太自私了,都六十五年了,他们就算死了也正常,而我却因为脸上的这条疤,怕他们也容不得我,而忽略了这点!
笨啊!
可是难道真的全死了吗?
我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啊。他们就算死了,可他们的后代呢?就算连他们的后代也死了,那他们后代的后代呢?
或许,可能,大概,是……
是老天爷容不得我吧!
步履蹒跚东向看,一亭在天边,那亭,名叫“思念”,那亭,专为我而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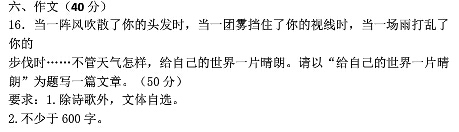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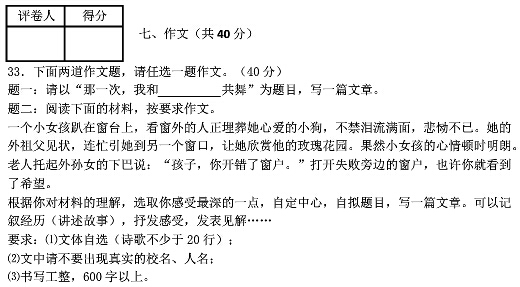
 小螺号弟弟弟弟吹
小螺号弟弟弟弟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