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一位对这电脑静静赶稿的作家,他神情漠然,只有手指在飞快地敲击键盘,在他一口气打完2万个字后,终于吐了口气,身子往柔软的椅背上轻轻蹭,斜眼注视着巨大的落地窗上反射出那点隐约的身影,与深夜上海依旧璀璨的灯火蹂躏成一团模糊的氤氲,渐渐的想要融入这个华丽的背景。
下一个镜头定格在世贸大厦,那些挎着LV包包穿着Prada衣服的女人踩着10m高跟鞋在光洁的大理石地砖上走得像个模特,男人的鳄鱼皮包里有掏不完的名片,那些卡片上的名字,就如他们的脸平面而空洞。在这幢金属建筑里能迁动他们面部神经的就是那一根根爬上爬下的线,他们的心也随之折扭,弯弯曲曲,像蛇一样。
再来,桥洞下有几个穿着哈韩的年轻人,如果你高兴可以把他们想像成是朋友间组建的乐队,怀揣着共同的梦想奏响了青春之章,那些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兴奋与不安,这是一场Game的开始,紧张又刺激着他们对未知前途那颗期盼却脆弱的心。
很多次家庭聚餐的时候,看着那些衣领上耸了一大堆毛的阿姨,我都会避而远之,那都是些什么三姑四姨还有他们的远房亲戚,我只象征性地冲他们一个甜得发腻的微笑,如果这表情被我身边的妖孽们看到了,不知道会怎样鄙视我。而不厌其烦的敬酒结束后,那些大人们开始闲得发慌,聊起他们出色哦应该是杰出的儿女,我只顾埋头夹菜,转盘上重重叠叠的盘子与它们刚被端上桌时的分量差可以忽略不计,我心想多可惜呀,所以拼命地让小鸡小鸭小鹅小蛙等革命壮士在我胃中永垂不朽。“安葬”xxxx红烧鸡排时依稀听到谁的大女儿快从英国回来了,二女儿还在犹豫留学是去美国还是墨西哥,当时我以为墨西哥是美国的一座城市,所以不堪重负地发出了类似与干呕的声音,但也只有那么一下,身边一个化着妖怪妆很容易被人怀疑刚吸完血的女人端起了酒杯:“哟,怎么没注意这儿还有位小朋友啊,来来,阿姨敬你一杯,祝你学习进步,这次考班上几十名啊?”我最讨厌谁在吃饭的时候问这个容易被呛着的问题了,而且,像我,这种语文考试基本靠感觉的人都觉得,她的语序是不是搞反了,要不怎么听起来挺不顺耳的,但又不能辜负了她对我那么妖娆的笑,于是大声说,还好,没被甩出前十。
本来这成绩也不是很好,估计只是他们从未从自己儿女那里听到过,所以失望又尴尬地夹了片黄瓜放进嘴里,其余的女士也捏了捏手,我猜他们已经准备了一大筐安慰我及鼓励我的话,于是他们再次无视了我,继续着美国好还是墨西哥好的问题。
他们,是一群和我毫不相干的人。
他们,是站在舞台上自我旋转的人。
他们,像水晶球里虚幻的影片,投映在我们圆圆的,深深的瞳中。
他们身上那些尖锐,淡定,丑恶或者单纯的东西,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我将来是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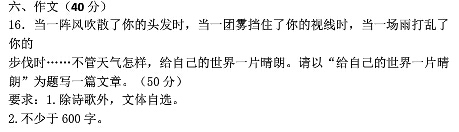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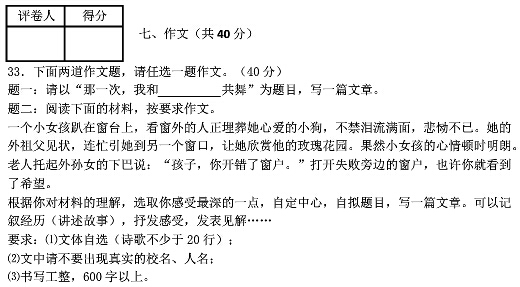
 iiikeaaaa
iiikeaa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