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在陕南的一个小村落里,交通闭塞。我的视野里只有四面林立的黄土山和零星卧在山坡上的土窑。我每天在上下学的路上唱着信天游,用羊鞭子抽打着路旁的花椒树,回家就着醋吃一个手瓣油膜,这样的日子里的希望仅仅是一台旧电视机里来回滚播的繁华都市。
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上海游玩,山村里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早激动得无法自己。往日在电视里看到的黄浦江、电视塔的映象在我眼前浮现。可昂贵的火车票像是一泼冷水浇灭了我心中的激动。我心不在焉地从学校挪回了家中。
父亲正在小炉前煎药,才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早已被岁月的霜白沾染了鬓发,俯下的身子像是正在药壶中受尽艰熬的蝉蜕,腰背还不时翕动着,发出降降干咳。他的手指夹着一只竹筷,另一只手执着蒲扇扇小炉的火灶口。我家的生计正像这间弥漫着中草药味的房间一样苦楚。
我嗫嚅着,吞吞吐吐地从嘴里往出蹦字,当他听到“去上海”时,他终于回头看了我一眼,几绺发丝沾在他的前额,空洞的眼神射出几屡光。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便后退了几步,打了几个咳嗽,去羊圈里拔山羊的胡子。
那天起,我放学后都不会看到父亲伏在小炉前煎药或在土炕上看方书,他总是在日薄西山时背着满满一筐枯枝烂草,夹杂着粪便的臭味。他有几次还摔倒了,碰坏了手脚。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本来充满着苦味的土窑夹着臭味,只发现他的背更弯了些。
那天,正是同学们出发的日子,全校五十多名师生借用了好几辆拖拉机都去城里的火车站为那几位同学送行。我兴奋地看着他们,干枯廋小的身躯裹了鲜艳的新衣,拖着涨得满满的帆布包,笑盈盈地向那几个家长告别。我有点心酸,仿佛是落群的丑小鸭在羡慕天鹅。“蓝娃儿”我听到一声急促地呼唤,四下张望着。远处正是父亲挥着手跑过来,拖着一个时髦的旅行箱,攥着张红色的火车票,我清晰地看到那是一张目的地为“上海虹桥”的火车票。他把车票递给我,我在那一瞬间清晰地看到他的脸,略显肥胖的脸上带着疾驰岁月的疲惫,眼角布满了白驹过隙时留下的蹄印,就像是缠满了蒺藜藤。他忸怩作态地说了声“快上车吧!”此刻,我多想再看看他的脸。
火车的汽笛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嘶鸣,我捏着车票上了车。车渐渐开动,我看到他还在向我挥手,蓝灰色的裤子上有些石灰蹭到的白印。我放佛蓦地明白了什么。回眸时,却看不到他筚路蓝缕的身影。
红色的车票在我手里被汗水浸得有些湿润,在奔向远方的时候,我没有放下那张车票。我想到了那一筐筐发臭的草药和与建康渐行渐远的父亲。此刻,我放佛是一个襄囊充盈的富翁,我有一间苦涩弥漫的土窑,有一张浓墨印染的车票,有一个不再若即若离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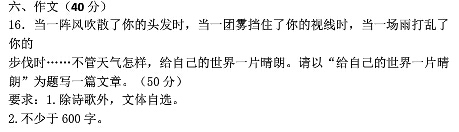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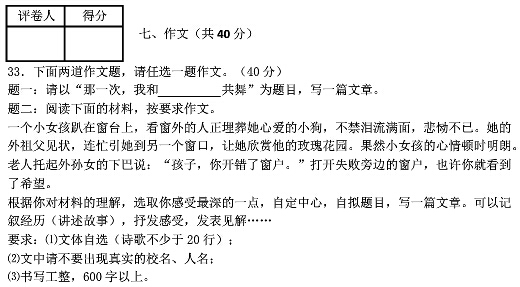
 我有病-你有药吗
我有病-你有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