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凄厉地照亮夜,城破时天边正残月,我喊她的名字,直到声嘶力竭,那一瞬,她那血染的眼,镌刻了这个国,倾尽了这一生的回忆。
我还在这守着夜,我还在这儿等着她,我还在这儿回忆那最亮丽的风景。
烽燧上,战烟袅袅升起,黑云还未散,聚聚拢拢,冷风一阵,又是一般翻滚。雨打得这座城这般寂寥,一座空城,一座死城。战旗已半,那是国破,君逝。我静静的看着那城墙,那头颅高悬,那满眼的情思。
兵临城下。血色的风肆虐的撕扯着战旗,翘首觐向,她伫立一方,一袭银甲在血色漫天中熠熠生辉,这双污浊的眼里,映现的是她那坚定不移的目光。她回首,对我笑,一瞬,我仿若觉着,那笑太过苍凉。她对我说:破了,就把我葬了,在这片国土之上。我不过是,一个守夜人,然而,我终是没有拒绝她。然而,我终是负了她。
敌军来势太猛,取这弃城,不过掌中烟。风霜打尽红墙绿瓦,她紧握长枪,红缨随风自飘,城中没有百姓,没有士兵,没有将军,只有我,一个守夜人,只有她,一个女将。这儿是我的乡,死也要相伴,这儿是她的国,死也要坚守。没有月光,没有残星,我的眼里却是光芒乍现,她执枪下跃,一个轻巧转身,落在了那边黄土之上。风披飘起,三千青丝风中张狂。她只身一人,黄沙未遮她的身影,风雨未褪她的坚定,黑云未隐我的视线。
银色的身影没入三千轻骑,耳畔杀伐不歇。那焚成灰的蝴蝶,那断了根的落叶,那染血的青石长阶,一下又一下将我这双污浊的眼装满。战马狼烟,肆虐残杀,她就那么一个人儿,银甲已被红染,青丝如墨,却有红色蔓延,血滚落尘那样艳烈。她终是厉害的,没兵,无马,只一红枪,但取百人首,她终是无力的,轻骑三千,岂她一人能当?我闻到,她的伤,将,注定难偿。
城头的灯终于熄灭,鲜血流过长街,三千士兵只余寥寥,我挣脱眼眶中冻结的悲切,努力的想将她看清。雨冷了我的眼,冷了我的心。银甲已成红裘,墨发滴血,赤足沾地,断刃入尘,殷红的手,手掌居上,似要抓住什么,却终是无力垂下。她的眼,她眉目染赤,看着我身后,竟是满满的情思。
我猛地转身,战旗血染,却终没倒下,她,也没有倒下。我歇嘶里底的喊着她的名字,贯彻九霄。黑云不忍,冷雨呜咽,一直坚守的土地在她的脚下,至死不渝的呼唤,月夜乍现,残星掩露,我伸手,手心上亘古的月光,抬起面容,多少能人巧匠书画三千里,却释不了这一刻的美丽,我终是没能诠释,那一眼,她满心系国,她笑如昙花,转瞬即灭,却是这世上最亮丽的风景。
断刃旁,岁月悄然的流淌,不记得阴晴或圆缺,不记得花开或花落,王城的姓氏都已改写,盛衰的荣辱都已斑驳的我的脸颊,千载已过,我已洗净铅华,等着命运的轮回。
我还在这儿守着夜,我还在这儿等着她,从灰烬里面,破茧成蝶,我还在这儿回忆那世上最亮丽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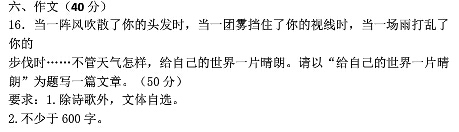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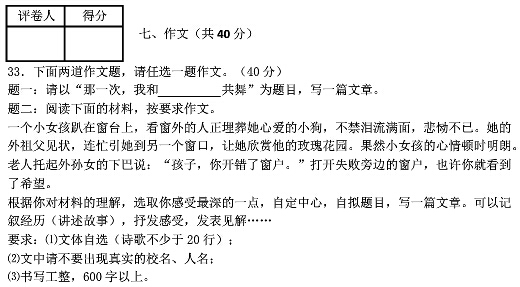
 Arpat-
Arp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