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墙,是老家那堵矮矮的墙。祖父从午后的山里挖来几十块有他两个头那么大的石块,在鸡圈边忙忙碌碌,从夕阳绕上山腰直到夜幕降临,才堆成了一堵好墙。
我爱极了这堵墙。白天的时候,我就从家里搬来木椅,像蜘蛛侠似的,“蹭蹭蹭”三连跳,片刻间就飞到了隔壁庭院。当我抬起头的时候,十几张笑脸映入我的眼帘,见最后一个伙伴到齐,纷纷大喊:“走喽!”我们像脱了束缚的猴群,跨过大山,滚过泥潭。知道月亮挂上柳梢头,才伴着月色缓缓归家。
夜晚的时候,那堵墙也给我带来极大的乐趣。老墙那么厚,可却薄得像一张纸,隔壁总有细碎的声音飘入我的耳中。女人会絮絮地诉说家长里短,仿佛那些事儿永远说不完似的。男人却早已盖着枕头,呼噜打得震天响,偶尔也会有小孩闯入房内,哭着喊着“一起睡”。我悄悄将脑袋顶在墙上,在窃喜中入梦。
后来的墙越来越美,也越来越厚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砖整齐地叠起,一桶又一桶的水泥精心地染上。在一切的最后,还要再向前上一层细腻洁白的瓷砖,才大功告成。
自从搬到镇上,左右邻里彼此之间似乎都是陌生人,没有人特地来拜访,更无人在街头巷尾悄悄谈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谁都来去匆匆,可整个世界仿佛都已冻成坚冰。
有一回,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寒风吹得凌冽,如尖刀似的扎着过路行人的脸颊。我到了家门口,搜遍了全身上下,可钥匙却不见踪影。我仿佛被放在火上炙烤,心头闪过无数可能,却始终无法想起。我又冷又饿,终于鼓起用起来,到隔壁敲了敲门。对方似乎在门后捣鼓了一阵,就不再有动静了。我垂下手,却突然想起一个冷笑话来: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你即使在街上大喊,也不会有人理会你的地方。
直到妈妈回家给我开了门,我才得以解救。
晚上,我习惯性将头抵在墙壁上,盯着黑乎乎的天花板,耳边寂静无声。
初三:古川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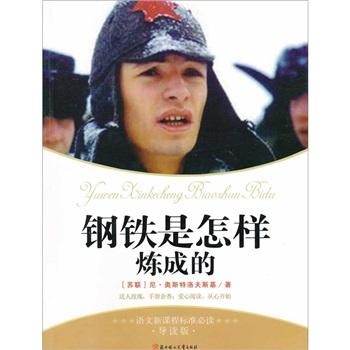
 么么哒打么么
么么哒打么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