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多有泼墨江南图,却从不见速写,嶙峋速写写不出江南的斑斓万丈;也不见油画,写实油画画不出江南的一片荒芜。这斑斓与荒芜,毫不相干的二词却成为江南独一无二的特殊记号。
说起江南之斑斓必先说流水,它们徐徐缓缓绕城漫步,百转不回。那些乘着乌篷船扬起皓腕采莲的女子,漆黑的长发倚着肩膀倾泻下来,然后悄无声息地投入水中。那些发丝的影子荡漾在荇菜里面,像是他们低低的吴侬软语。偶尔有燕子斜斜地掠过水面,最终也隐没在水边黑色的屋檐。汨汨的水声在尘嚣褪尽之后显得更加清晰,当初,古城的建造者一定深谙水的灵性,将山泉引入城中,命人在水边栽上杨柳,使小城变为清丽的水乡。长久生活其中,清冽的泉水也淌进了江南人的血液,使江南人变得细腻起来。养花种草、迎风弄月,刀枪演变成了笔墨,战场上淋漓的拼杀演变成了一行行遒劲的书法、一幅幅清秀的花鸟工笔。这样的风雅绵延了几百年,如环城细水潺潺不息,极尽江南之秀丽斑斓。
走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上,听着悠悠绕梁的小调,抚摸着那一面面刻满了历史的石墙,一股伤感油然而生:原来,在江南斑斓背后也有荒芜至此。“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倚楼凝望的思妇,恨不相见的商贾发妻,江南的荒芜溪流是多少无可追溯的香泪,江南的荒芜青苔是多少少女孤独垂老的褶皱。那拎着酒壶,乘着渔船,一面酌酒赋诗,一面赏山赏水的两人是谁啊?原来是唐伯虎和祝枝山。世人素来听闻二人无意于功名,只只结伴野游、唐画祝字、寄意芳花于江南。却不曾得知唐寅从京都因陷害而回看到江南的烟波心中却只徒有一片悲凉,听到江南的浅唱却只更添伤悲。也不曾得知,祝枝山因此辞官却让荒芜的江南更映现出彼时天子脚下的无边黑暗。
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为江南找到一个妥帖的记号保存心底——那会使它黯然失色。然而,斑斓与荒芜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却在江南得以完美统一,撞出摄人心魄的美丽。每每记起江南,总想回想起斑斓的流水清歌和荒芜的人文关怀。
“灯影桨声里。天犹寒,水犹寒。梦中丝竹轻唱,楼外楼,山外山,楼山之外人未还。人未还,雁字回首,已过忘川,抚琴之人泪满衫。扬花萧萧落满肩,落满肩,笛声寒,烟波桨声里,何处是江南。”
初三:津度度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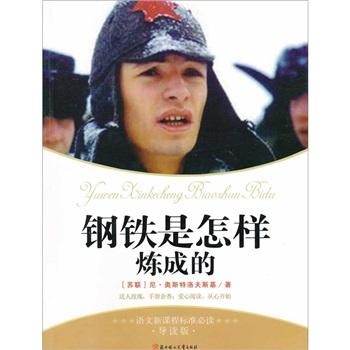
 悟空去搬砖
悟空去搬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