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莫春秋
年华里,终将有人走远——题记
小城
小城,总是有一种很宿命很暖心的感觉。就像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怀旧的背景总像某种电影脚本里的经典辅陈。斑驳的旧城墙,岌岌可危的筒子楼,菜市场市侩的谩骂和方言,一起维系着这座北方的小城,栖满了小小的幸福与忧伤。
我在小城里长大,十三岁以前世界也只有那么大。我从小听着天边地平线上疾疾掠过的飞鸟的叫声,一声声紧紧贴在塞北昏黄的天空上。奶奶总是坐在土炕上,笑容充满温暖的槐花香味。我听着从她口中衍出那些支离破碎的民间杂史,觉得窗外的风景像是一副年代久远的画,沧桑的如同风雨飘摇的宋朝。
邻居家有个老爷爷,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拉他那把落满尘埃的二胡,声音苍凉深远,荡漾在风沙细腻的小城里,最后在风中弥散。他的孙子却有一把吉他,夜里弹出清越如梦呓的乡村音乐,音符如在寂静中起舞的精灵。
偶尔会在下雨时,看书着了迷。抱着从二手书摊淘来的盗版《追忆似水年华》,拿着一袋麦烧。走过巷口,看见那个男孩挽着我奶奶在巷口等着我回家,他们身后的夕阳像被撕裂的莲花,奶奶则永远像提着灯的慈母,等风尘仆仆的游子归来。
载着这些记忆我在小城里慢慢长大。从小到大,骑着一辆旧单车,和邻居那个叫韩煜的男孩一起上学,放学,从小学到初中。
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那些桃花开遍的日子。在蒙蒙的雨季和纷扬的雪中,总是两个人一起出发,最后一起回家。我很喜欢这种青梅竹马的感觉,像苏童和安妮宝贝笔下的宿命。我喜欢听他弹吉他,抬起头就可以看见天上的星光像扬花一样萧萧落在他的身上,日子就这么安静的盘旋在城市上空。一点一点淋湿了那古老到石头都开始风化的小城。
我以为这种青梅竹马的浪漫会像轰隆隆碾过的岁月一样永远不会结束,就像韩永远弹不倦的那首Avrillavigne的《tomorrow》。我想当我一无所有垂垂老矣时,只要有朋友和吉他,我就依然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人。
那些冗长,迷幻,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年华,大抵也会像留念里一叶扁舟,默默游离然后搁浅,最后沉淀的悄无声息。
莫
晚风携着青草特有的香味撂动面颊淡淡地隐在了身后,燕子衔着绿色匆忙的飞行。韩站在香樟树的阴影里,白色的扬花不断落到他的身上。我知道小城的春天正在渐次苏醒,抬起头我可以看见苍蓝色的天空,那个大大的太阳,依然每天在这个小城升起,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再缩短。
韩煜中考结束,在陪他等成绩下发的日子里,我们家属院有一个男孩在黑色的高考中脱颖而出,以全市理科状元的分数考取了清华大学,小城,在一夜之间斗转星移。
荣誉、采访、精致的物质奖励,在那个夏天的黄昏闪亮了我和韩煜的眼睛。
偶尔会在一起谈论一下我们看似并不遥远的梦想,他的爷爷总会拉着二胡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们成了听话的好孩子。被许诺将来有糖吃的好孩子。我们坚定地做那个安静的读书人,窗外的雪花和雨水与我们无关,与梦想踏进清华园的我们没有任何关联。
在那个雨水充沛的夏天,奶奶病危被叔叔接到南方治病,她病得已经很重了,可是一直拖,叔叔屡次劝她搬去南方,冬天时就不会再犯哮喘,可是奶奶说,这地方她住了几十年了,不想走啊。
奶奶的肺病很严重,在冬天常会咳得半夜难眠。她难受得像人死去时灵魂被割离身体,带着恍恍惚惚的留恋和未知的恐惧,奶奶告诉我,每个人在死的时候都会回到自己的故土,落叶归根,否则就会成为漂泊的孤魂。
然后奶奶说,你其实是出生在江南,我在你百天后才把你抱回这里。
从来都没想过离开小城的我,一直觉得小城是我的根,离开故土的每一步都会异常疼痛。
奶奶离开后,我忽然会在梦里哭醒,泪水从梦里流到梦外,我号陶大哭,我梦见奶奶去世了,韩煜只是揉揉我的刘海,说人啊都是在自己的哭声里开始,在别人的笑声里结束,这中间的时间,就已是足够的幸福。
几天后,我也被叔叔接到了南方,当我到达浙江杭州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有细雨开始从天空缓缓飘落,那些风景很美,像山水画中介于泼墨与工笔之间,蒙了一层氤氲的水汽,走进石桥时我感觉我就像个宋朝伺人,长衫迎风而立,满腹心事地低吟浅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雨打窗台湿棱梢。
这就是我的故土吗?我看着那些满天飞扬的纸茑走过岁月流转的雨巷,但我却更想念萧杀的塞外小城,古道西风,飞鸟,芳草碧连天,夕阳山外山,腰鼓、秧歌和驼铃、都是魂牵梦绕的乡音。
我终是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我仿佛听到我的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
父母从外地赶回来处理奶奶后事的几天我可以到处闲逛,我去了浙江大学,我望着那些大理石的白色建设目光变得有点模糊,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家,在她的面前我似找到一种归宿,我不是浙大的学生,但我却想成为浙大的学生,这就是我和浙大目前惟一的联系,有点像单相思。
当我回到小城时,中考的一切尘埃落定,韩煜以全校最高分数落户到北京的重点中学,走得那么仓促,那么缺少理由,而生活很多时候真不需要缘由。
北京,只是一个城市的名称,在我的认知里除了天安门是清华大学,如今又多了一个他。
夜寒如水,眼前闪闪烁烁过奶奶的心电仪那一声波形回归直线的长音,韩煜的爷爷拉“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而他微笑时多么温暖多么好看,还有杭州,西湖畔的浙大,像梵高的色彩如沐霖打湿的粉墨涣散开来。
我抬头看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伤心是岁月交给成长的税,疼痛是回忆与成长协定的契约。
我走过月台,穿过海一样的麦田,夕阳下的我翘首期盼,还是在做一场无名的祭奠。
春秋
初二暑假结束的前一天,一位老师对我说,生活带给我们太多逆境和磨难,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只要太阳能照常升起,生活就还有希望,只要你愿意积极地在吸收正能量,重新认识爱,接受爱,追逐爱。你就一定能在悲伤的黑暗里走出来,迈向光明。
当我见到她本人时她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也是小城三年前一场车祸中为救学生失去一只手臂的青年教师模范。
我开始打开心扉,奔跑着追求我的梦想。奶奶说过,纵有末日,爱天尽头,每个人都无需沮丧,只要你心中有爱。
在这之前我因思念奶奶病的很重,高烧不退。感觉自己没有活下去的力气时,梦境里奶奶用土办法烧草纸冲水,说,大孙女别怕,会好起来的。本来以为目睹过杭州的繁华后会不屑于小城和土房的颓败,可是在生死边缘的时候,又记起来,而且带着沉甸甸的暖意。就像童年里我从不害怕夜路,因为我知道车转过巷口就会有奶奶在那里等我回家。炎樱说,每只蝴蝶都是前世的花魂回来寻找她自己。我想我就是千年前拂过小城的风,奶奶就是那我轮回永世不忘的黄沙。
《圣经》里说过,在遥远的亚拉腊山上会下红色的雪。在一个火烧云的黄昏,小城下起了罕见的微红色的雪。韩煜背着他的吉他回来,带着一个女孩儿。他摸摸我的头,嘴角上扬露出朝阳般的笑容介绍说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妹妹。他身后的女孩说:“你好”笑容如同樱花般明亮,眼睛里是掩不住对他的爱慕。
小四说过,我不知道以后的时间还有这么长,长的足够让我忘记你,让我重新喜欢上一个人,就像当初喜欢你一样。慢慢地长大,某些懵懂的想法开始慢慢消退,最终销声匿迹。就像自以为是的青梅竹马的爱情传说会在我身上延续,如今想来,是多么无知。依旧不变的真理,还是那些似锦的前程与梦想的腾飞。让那些青春的疼痛与轻狂就随着时间的流逝永远的沉浸在海底泡沫里吧。
启程时韩煜弹了一首《Dreamscometrue》送给我。我听着清亮如溪涧的吉他声,想起了一句日剧台词
——总有一天,星光会降落到我们身上。
“韩煜哥,明年高考,祝你南下帝都一切顺利。”
“你呢?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我会在那里等你的么?”
我笑了,“只不过,我要考的是小清华。”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觞。
中考前几天我站在小城的最高峰上,那座小城其实并不小,即使我的故土是在清流秀影扬花的江南,纵然它是迁客骚人笔下的“感极而悲者矣”的塞外,它仍然是我化不开的土地情思,温柔的深爱记忆。
也许我会把小城的露天煎饼摊和奶奶煮的面条里的胖鸡蛋装进行囊,带着它们远走他乡,那是我不能割舍的乡情和血脉。
泪痕不会永存,青春将是一道不老的风景线,奶奶会在开满葵花的云端注视我和我爱的人们前行得更远。
到那时,连向日葵都会转向我们,和我们闪闪发亮的青春。
初三:徐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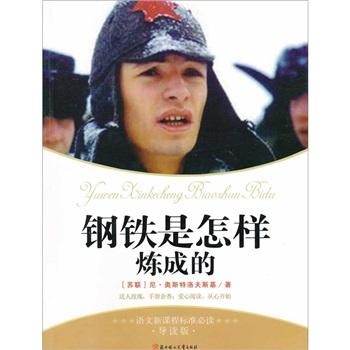
 怎么什么好么30225486
怎么什么好么30225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