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爷爷找出一堆旧照片,将一些非常简单的字写在它们的背面,比如“人”、“大”、“天”、“田”、“土”、“雨”,教我这些基础的内容。然而每当我看见这些卡片的时候,便会将它们翻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看。爷爷发现这些照片太分散我的注意力了,于是将中文字写在裁好的广告板上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与他一起背唐诗也非常简单——因为那时我认识的字不多,无法使用教材,所以爷爷自己抽时间一句一句地教我。他教一句,我跟着重复一句。
一段时间之后,我便可以背下整首诗,包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不过,那时我并不理解这些优美诗句的深刻含义。到了美国,我跟着妈妈学了一点中文,我们从中国的小学教材学起。大约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教我学中文的差事转到了爸爸的手上,从那时算起,我已经跟着爸爸学了十年的中文。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背生词,写作文等等。就连爸爸出差的时候我也在学习:他给我布置好作业,然后打电话回来检查我的功课,不给我任何一个偷懒的机会。我在旅行的时候也要学习,我已经习惯在出门前将教科书放进背包里。爸爸教我中文的方法比较特殊,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学一门语言要求学习听、说、读、写;与其在这四个方面同时下力,不如将它们各个击破。听和说是交流的基础,正常人都能很容易地掌握它们。
在家里我们说四川话,看中文电视节目。因此,对我而言,听和说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有新的中国电影上映时,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去看,比如: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和李安的《卧虎藏龙》等等。撇开听和说的练习,爸爸将重点放在教我读和写上。因为他说:“读和写是人类交流的高级方法,可以增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爸爸一直让我做一本综合练习册中的练习。此外,他还找来很多短小的故事,让我在课余时间里阅读。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本中文版的《读者文摘》。一开始,爸爸挑选一些容易的短文给我看,或者跳到“笑话与幽默”的版块。后来,由于我的中文进步了,便可以阅读长一些的文章了,这时我发现其中的一些文章优美动人。于是爸爸和我都成了这份精彩杂志的热切追捧者,几年后我们已经收集了整整一书架。我尤其喜欢像“心灵鸡汤”一类的文章,因为它们真正具有思想内涵;另外,许多神秘的和与动物有关的故事也很有趣。每读过一个故事之后,爸爸便会要求我提笔写下我的想法。
此外,中国的语文教材里也有许多关于写作方面的要求。比如,当读完一篇闻名世界的民间故事之后,我要为其写续篇;看过故事里的一幅插画之后,我也要写一篇短文;每次旅游回来,爸爸会要求我记述旅途中的见闻;在大部分周末我都必须写一篇作文。爸爸要求我使用刚刚学过的中文词句,甚至将一篇文章中最优美的语言运用到我的写作之中。其结果是我丰富了写作手段,提高了写作能力。这样的日积月累也成就了这本书。跟爸爸一起学习也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许多事情我坦率地与爸爸一起讨论。我们是父子,也是朋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学习之后,学校里的一些事情忽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会立即告诉爸爸,于是就展开了讨论。有时候,妈妈也会加入讨论,或者在听见我们大声交谈的时候,她会推门进来问我们怎么了,爸爸和我就会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们谈哲学都谈到21世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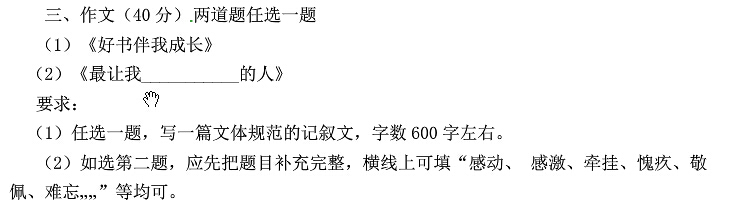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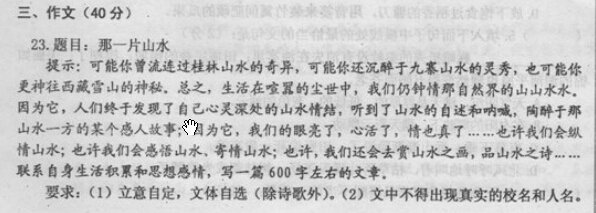
 愤怒的趣多多
愤怒的趣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