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拿够了吗?拿不够可怎么吃饭呀,筷子还没够,再拿一只。”妈妈又在指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野炊了!
虽然黄金周变成了“黄金粥”,但我不甘心在家呆,经过商量后,我们决定去“老婆寨”野炊。作出这个决定后我亲自打电话问问俺姨妈俺舅妈他们,他们听了我的“油嘴滑舌”之后也心动了,于是就有了刚才我们准备的那一幕。
俺姨妈、俺舅妈、俺爸妈、俺俩哥、阳阳和璇璇都来了。我爸是司机。为了这次野炊他连生意都不要了;别看我外公腿不好,去年上大佛玩的时候,他也硬是上去了;阳阳和璇璇小,爱跑爱玩,不过璇璇有点小,走不动了就让舅妈抱着;俺森森哥上高中,就是有点胖;我就不用说了,这胳膊里的小肌肉里可藏着使不完的劲儿;但我那位比我大十月的世博哥体质可就差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要出来走走。
我们乘面包车沿着蜿蜒的水泥路来到了山脚。我看了看,这条水泥路能通山腰但我爸说,既然出来了,就多走两步。我们很信服的点点头。于是各自拿着各家的包袱,向着山顶出发。
我们哥仨一路上有说有笑,我唱着山歌,森森哥拍着广告,而世博哥却累的气喘吁吁。俺姨见了,便心疼他儿子,说;“歇会儿吧。世博也走不动了。”行,歇一会儿。
俺舅妈手很巧啊,用路边的野花不知不觉就编了两个花环,给璇璇一个,给我妈一个。阳阳却拾了一个草帽。俺姨说:“你在哪捡的?”“我就在那儿捡的,我看没人要了,就拿过来”。阳阳支支吾吾的说。俺姨刚想开口,俺妈拦住说:“算了,那就回来还放那儿。再说了,咱阳阳带着还挺合适的。”大家都笑了,阳阳也笑了。
歇罢,又要赶路。森森哥带上草帽,还在草帽上安放了个花环,看着像特种兵一样,刚好那有一个坑,我幽默的森森哥就跳进去,随手拿了一个棍子当枪,指着阳阳:“小日本,哪里走!”阳阳也挺入戏,左跑跑右跑跑,还说:“花姑娘,我的花姑娘别拿枪指着我呀。”搞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们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山腰,那有一座庙,里面有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见我们来了赶紧递给我们凳子。外婆和这位老婆婆闲聊着。本来想现在就煮饭,但我爸说先爬山吧。问问老婆婆这里离山顶有多远,老婆婆说还有五里才到山顶。外婆说:“山上五里能比十五里,我不去了。”外公也不去了,璇璇呢,她太小了,也就没让她去。森森哥也很不想去,但我说:“减减肥嘛,这么胖!再不走就长不高了!”我故意将“胖”和“长不高”这几个字重读,因为我哥虽然上高中了,个子才超过我一指。所以他也去了,还跟我说:“让你诅咒我,算了,反正现在也吃不成饭。”
我和阳阳、世博在前边。世博还拿了个扩音器放音乐。“慢点!”“跟上!”这些矛盾的话总从我嘴里说出来。咱也是关心嘛。每到一个陡坡我都会喊这些矛盾的话,并停下来歇会儿。顺便看看周围的高山与脚边的深渊,奇怪的是,向来都有恐高症的我却突然不害怕了。等他们赶上来时,我便系好鞋带,继续向前。世博落伍了,瞧!他四肢都用上了。
走呀走,我和阳阳能看见山顶上的小庙了!我俩兴奋不已,跑着前进。“我上来了!我登上来了!”我俩在呐喊。我俯视群山峡谷,周围没有一座山比我高,我爬到山的最高处,心里很舒畅,很痛快,这毕竟是我十二年来上过最高的山呀!他们很快也跟上来了。我大口呼吸这新鲜的空气。一会儿,我又在小庙旁边剪脚趾甲,大家都在说笑。
我妈让我喝感冒药,我说:“感冒在上山时早就坠入了万丈深渊。”但我还是喝了。
在山顶上,我感受着风的洗礼:风把我的病吹走了;风把我的脚臭带走了;风把我的声音吹变了;风把我的身体吹壮了!
我们进了还没十平方米的小庙,庙中住着的“送子祖母”已等候多时,我连忙拜拜佛。
在山顶歇了一会儿便已是三点半,赶紧下山。人们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就不这样认为。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的:走哪条路?有没有蛇?离山顶还有多远?但下山时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自然轻松多了。所以我在下山时感觉很快。
在山腰,我们在老婆婆那里吃了面,与老婆婆告了别,就又唱着山歌下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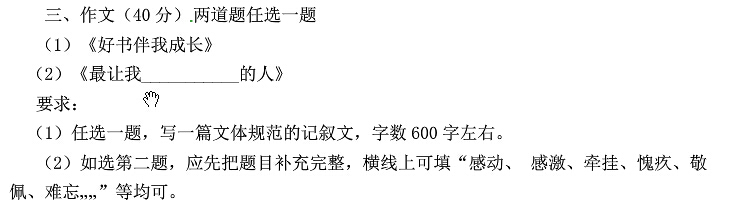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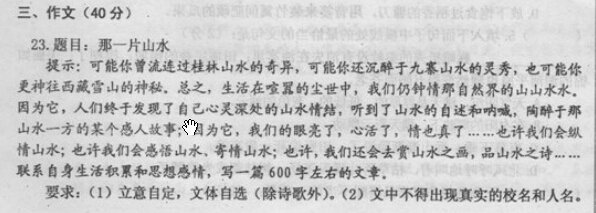
 听说污的人颜值都很高
听说污的人颜值都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