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飞疾而过,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条路,上次是这样,上上次也是这样,事实上,每次经过这条路,我都会这样看着……忽然间,又像是不知不觉间,没有了喧嚣,看不到汽车,看不到行人,全世界只剩下我,这条悠长悠长着向上陡的路,那些不变的路灯,还有摇曳着的树。
我一直看着路的前方,那是灯火通明的前方,两边整齐的路灯像两条闪闪发亮的钻石项链,一直那么闪耀着,从开始有记忆的我,到现在茫然着的我,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不禁想,那时我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记得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着这条陡峭的路,常常想,等我的车开到陡坡那里,一定会掉下来吧!于是我系紧了安全带,甚至准备随时营救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爸爸。然而直到下车我才意识到,那段陡峭的路早过了,我一直思考着,为什么经过时像平地呢?似乎每次经过时我都想到这个问题,小时候,我丢开那些所谓科学解释,看着路灯,**着脑袋思考着,用我自己的方式思考着。而此刻,我也**着脑袋思考,在恍惚的黄色灯光中……
回忆开始断断续续播放,仿佛还是昨天,我和朋友们在家办了一个小小的只属于我们的生日派对,吃完蛋糕,我拿着一张大纸,画着我们将来的房子。我说,我要把爸爸妈妈都搬进去,我们的家人都住在一起!她们点头赞许,其中一个还说,窗户要作成兔子形状的,墙要用巧克力做。我不同意,说,巧克力不好吃,要蛋糕做,如果摔倒了还软软的,不疼,摔在巧克力上一点都不舒服……我们那样认真地讨论着,那是多希望第二天就长大了,就可以去建我自己的房子!
那样清晰地记得和同学拉钩钩,中指是和好,无名指是分手,小拇指是许诺不说出小秘密,拉钩就像一种不可少的程序,没有拉钩就不能兑现。我记得一下课就跳橡皮筋是的疯狂;一起吃午餐谈天说地的快乐;给芭比娃娃做衣服的痴情;一起野炊烤鱼,拿树叶熬汤的童真;用树枝作秋千摔屁股的阵痛;围一大群在街上狂唱狂跳的痛快;加入表演队化妆后的自豪;被同学玩笑后找老师辞职的委屈……那些零碎的记忆,写不完,播不完。
我记得有一次疯玩后头冒白雾,朋友说是要成仙了!我吓怕了,赶紧跑回家抱着妈妈大哭,妈妈说那是因为水蒸发,我却一个劲喊着:我不成仙,呜,我不成仙,我要和阳阳玩,我还要当班长,呜呜,还有大队长……
我记得我们四个曾像电视中那样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结成了姐妹,一刻都不分离,上课偷偷换座位,我们无话不说,有时不需要说话,只需要在一起就有安全感。我认为有了她们就可以去冒任何险,我以为我们一辈子不会分开,可现在却再也联系不到了……
我听见爷爷问我怕什么,我重重地拍着胸膛,想象自己是奥特曼、葫芦娃,我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思索了一番,又加了一句,除了蛇和其他扭来扭去的虫子,我想不到有什么比回头看到毛毛虫更可怕。我告诉爷爷,如果看到老虎也别怕,我会保护他的,而且我还在不断直视太阳练火眼精金呢。他只是笑,我也只记得他的笑,那样慈祥的笑。后来爷爷去世了,只留给我记忆中的微笑,再也没有人问我怕什么,更没有人关心我怕什么。
一切那样清晰而模糊,那么多东西总是可遇不可求,我不知道我曾拥有这些经历算不算幸福,我只知道,那后来的现在,没有人再和我一起疯疯癫癫;没有人会担心我担心的;没有人与我无话不说;没有人一看到我就大声喊大队长;没有人了解我像了解她自己;没有人直视我的眼睛说还有我;没有人会原谅我所以的错误,没有人无理由地时刻和我在一起;没有人那样亲切地叫我。没有,再也没有。也许那些只属于过去,我只能庆幸这些存在于过去,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至少他们存在过,至少我还记得,还能偶尔温暖,在自己的世界再次拥有。
……
一眨眼我又回到车中,看着窗外,一盏盏路灯划过我的视线,如同这样,时间会带走一些东西,环境会改变一些东西,如果说一物换一物很公平,那么我想,我并没有失去什么。
在到达坡的最高点是,我望了一眼后视镜中的那条路,那些模样依旧的闪着温暖黄光的路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笑了,大概因为他们还是老样子,过去了的什么都没变,都还在那里,幸亏都还在。
我心中一阵满足,瞬间经过了那个平坦的陡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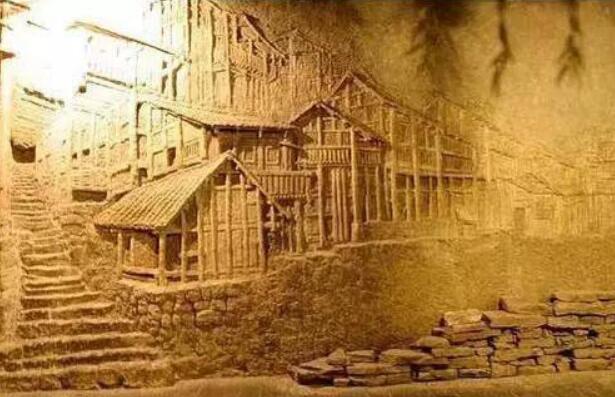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Mr点BUG
Mr点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