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藏在微笑背后,我们都在慢慢长大……
——题记
A筝,你听我讲
“兰,你听我唱首歌给你听好不好,我睡不着了。”你扯着嘶哑的喉咙十分“艰苦”。
我这个时候正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开着夜车,听到邻床传来的痛苦的鬼哭狼嚎,毅然决然放下笔,大义凛然掀开被子,摆出一副和你般配的神经病式痞子相,像要调戏良家妇女似的,拉着长长的尾音,“好啊,你唱吧,本姑娘就勉强欣赏欣赏你的歌喉吧。”
你就真的就开始唱了,沙哑着喉咙,竭尽全力地拼尽了吃奶的劲哼着,却还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换做平常,恐怕我是早就要抓狂了的,但是看到你神经质得都不同寻常,第一句话居然没有是在损人,声音又变成了这样,只觉得怕你生病了,声音竟是柔了下来。
“你没傻吧,脑膜炎留下后遗症了?你,你没事吧,有事你就打我好了,您老啊就是奥特曼,桑心了你就打我这可怜的小怪兽吧,诺,我还在这里啊。”
说完,我还故作深沉的长叹一口气,像古代读书人一样使劲地把脖子扭了扭,把脑袋摇了起来,却把手伸了过来,紧紧地握住你冰凉的那一双,心里也凉了,你这是发烧了吗?
你的嘴唇都发了白,勾起一弯淡淡的笑,带着那么一点点的欣慰,“好啦,我打你干嘛,我手痛……其实,是因为他们。”
我知道他们是谁,必定又是他们了,他们从你上初中起就开始不停的骂、吵、闹,弄得你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我条件反射地想要叹气,想又到你还在旁边呢,听到了该有多伤心,握着的两双手便是更紧了。
……
见你终于安静了下来,眼皮也惬意地合上了,终于放下心来,但是你的手还是那么冰凉,我疑心你是真的发了烧,摸了摸你的额头,滚烫滚烫的,我慌了,呆住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起身打了一大盆冷水,拿来了毛巾。
“谢谢你。”你魂一般的声音飘过来,在这黑色中蔓延开来,通过某种奇怪的介质传到我耳中,我还以为你昏睡得“不省人事”了呢,不过能说话就好。
“亲,警告你啊,你生分了哦。”我即刻换了一张嘴脸,威逼利诱起你来。
请告诉我,淡淡的青春会带走淡淡的忧伤,留下淡淡的泪痕,诉说淡淡的过往吗?你是不是会笑着流泪,哭着微笑,从阳光的裂缝中伸出手说,我们微笑?
B兰,你听我讲
“兰,你听我唱首歌给你听好不好,我睡不着了。”我忍着头的某一部位传来的昏昏沉沉的痛,故作精神,扯着嘶哑的喉咙十分艰苦。
你是一个闪耀着烁烁光芒的大学霸,众多向我一样的平庸人眼中的超级大神,这个时候肯定正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开夜车,我本想着你不出来就算了,但一会儿,就看到了你从被窝里探出来的一个圆溜溜的脑袋,嘻哈的脸上摆出一副和我极配的神经病式痞子相,像要调戏良家妇女似的,拖着慵懒的尾音,“好啊,你唱吧,本姑娘就勉强欣赏欣赏你的歌喉吧。”
我狠狠地想,我便是不要这个嗓子了,于是真的开始唱了,沙哑着喉咙,竭尽全力地拼尽了吃奶的劲哼着,却还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换做平常,你恐怕是早就要抓狂了,但是你居然没有。
“你没傻吧,脑膜炎留下后遗症了?你,你没事吧,有事你就打我好了,您老啊就是奥特曼,桑心了你就打我这可怜的小怪兽吧,诺,我还在这里。”
说完,还故作深沉的长叹一口气,像古代读书人一样使劲地把脖子扭了扭,把脑袋摇了起来,却把手伸了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那一双,好温暖。
我牵起呼吸得发了白的嘴,想笑,可是无奈,皮肤绷得太紧,“好啦,我打你干嘛,我手痛,其实,是因为他们。”
我的思绪开始松弛,像放电影一样,事情一件一件地掠过,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你知道,有的你不知道,我想把好多好多你不知道的事告诉她,可是,渐渐地,好几部电影一起放映了起来,我只觉得力不从心,讲了也必定是语无伦次的,只好就罢。意识坠入了无底的深渊,我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一点一点消逝在这浓浓的墨色当中去了,可是为什么在这时,指尖的温暖无影无踪了呢?
……
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一只手在抚摸我的额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掉那只手,可是身体太沉重,动弹不得,我感觉我想已经躺在太平间的大冰柜里了一样,周边全部都是没有呼吸的僵硬的尸体,四周缭绕着模糊的雾气,一片氤氲。
我感觉,有一块冰块敷到了我脸上,我的身体没有那么沉重了,两片紧紧亲吻着的眼皮可以慢慢分离了,我看见那冰块幻化成了一个毛巾,皮肤接触的冰凉也觉得是温暖。
“谢谢你。”我使劲一拔,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上嘴唇拔离下嘴唇,细细的说。
“亲,警告你啊,你生分了哦。”你真好啊。
我想,幸福是可以从天而降的,当我们牙齿全都掉光,头发斑白,垂垂老矣是,我依然会记得那个夜晚,我的高烧,我的语无伦次,我从你那里要来的温暖……
友情是糖,我们不要甜到悲伤,我们一起吃就好了。
作者依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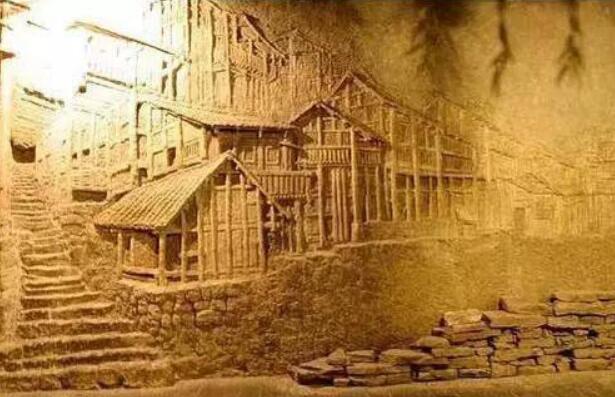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用户24274846
用户24274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