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人们,黄土地上的生命。不知是谁,点燃了青石墓碑前的烟火,一世的欢乐与辛酸,只化作一簇火光,直冲漆黑的云霄,划破天空的脸,流出一摊鲜红的血。那是耀眼的火光。
难割舍
参加了一个葬礼。
一辈子面朝黄土的老人,在悄无声息深夜的一团漆黑中平静匆促地死去,甚至于还没来得及呼唤儿女的名字——抑或是喊了,只是他们没有听见罢了。
葬礼上,人们纷纷猜测她的死因,哀叹她的不幸。唯有与她情同姐妹,一辈子同甘苦共患难的奶奶,无言,傻傻地站在黑得不能再黑的黑木棺材前,她呆呆地盯着她最后的留恋。
高高悬挂在大堂的是一张黑白遗像,相里的人咧着嘴开心地笑着,年轻洁净的脸上略显稚嫩,那时的她该还是没有历经过生活的艰辛的吧,怕是在她开始触及到生活锋利的刀的冰凉的时候开始,慢慢地感受那把刀渗入自己的肌肤、脂肪、血管甚至是心脏的时候,就再没有照过相了——她那公事繁忙的儿女们,自然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
奶奶眼眶红着,眼袋显得愈加沉重,止不住的泪越过高高的颧骨,顺流而下,缓缓滑落,在干枯树皮似的皮肤上流淌过,河流两岸长出翠绿的草,开出鲜艳的花,飞着翩然的蝶,让人惊喜而又惋惜。
泪惊醒了沉寂在美好回忆中的奶奶,她连忙抬起苍老的手,轻轻把泪拭去,皱巴巴的干若树皮的皮肤之下,一根根触目惊心的青筋像一柄柄透着寒光的利刃,卯足了劲一下一下刺在我还涌着大片大片献血的鲜活跳动着的心脏,我吃痛,别过头去,听见奶奶低落的沧桑的声音:“你走慢些,我很快就去陪你了,你在那边缺什么要什么尽管托梦给我,我一定会捎给你的,你别觉得孤单就好……”奶奶有些语无伦次了,右手撑着腰,艰难地弯下身子,撕开两三张钱纸,向火光抛去。火光闪了一下,像躲闪着的眼睛,不愿目睹这一切一切的难以割舍的无奈。
火光耀眼,却不暖心。
乡亲们连忙来搀扶奶奶。
接着,我听见了嘈杂锣声下老人儿女们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戏
昨晚的戏台子,道士的幕布都还未来得及拆掉掀掉,但看这残局,便可马上知晓昨天的“晚会”是有多么的盛大了,就像一个在cosplay化妆舞会上浓妆艳抹的女孩第二天早晨的残妆定不会是淡淡的。
几个身强体壮的中年汉子腰间绑着白色的缎带,面无表情生硬地抬着那副有着灿烂的五彩幕布装饰的黑木棺材准备出殡了。
我听见有乡亲在感叹棺材的名贵的珍奇。
她的儿女死死地抓着拖着,神情痛苦地挣扎着旁人的拉扯,不让老人离去,大颗大颗的泪滴像坏了的水龙头似的哗哗直往下流,关也关不上。就好像他们的妈妈是整个宇宙的曙光,一旦消亡,这个世界将万劫不复,所以他们如此敬仰她,舍不得她。可实际上呢?
早些时候听闻,这一大家子甚是不团结。三儿一女推着壤着就是不肯给一双老父老母赡养金,而老人只好和老伴在简陋破旧的瓦房里,靠着政府少得可怜的的补贴和邻里得来不易的施舍过活。着这瓦房里,春天潮湿,仅剩的馒头都霉掉了,夏天多暴雨,这房子的瓦破破烂烂,每一块完整的,就像一个秃顶的老人,下雨了总是他最先知道,秋天,风凉飕飕的,这个房子就化身为路边乞讨的可怜的叫花子,穿也穿不暖,不是上衣的袖子破了一个洞,就是鞋上穿了一个孔,冬天,风更狂了,嘶叫着,好像他才是世界上最遭罪的人——分数不高、长相不好、还没零花钱,怒起来又掀了几片弥足珍贵的瓦去。
在这样的环境中,老人在与儿女打官司之际逝去了,哪能不引得议论纷纷?
不知是谁点燃了烟火,一朵朵开得正热闹的略带戏谑的火花之下,她的儿女开始送她上山了。
鞭炮声连绵不绝,好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噼里啪啦响一阵,消停一阵,又噼里啪啦闹起来。
她的大儿子手捧她黑白分明的遗像,虔诚的模样走在最前,嘴里还不停的在念叨着什么挽留的话,却自顾自地大跨步往前走,也不顾这个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到底跟不跟的上,他的灵魂到底跟不跟的上,好似他只是在完成一个心里不情愿却又必须得装得很在乎的无关痛痒的仪式而已。
她的老伴披着洗得起来皱痕的单薄的白外衣,畏缩着在这早晨冰冷的泪中,走在长队的最后。他清凉的泪划过冰冷憔悴的面容,眼眶里泛着红。
一路上,他们都没有说话。
你的挚爱,我的挚爱
下葬结束,奶奶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回着头不舍地望着。她怕再也看不见了。
大概这就是生命,总是那么脆弱,好像芦苇,一折就断,好像珍瓁,一触即碎,好像空中的火光,瞬间的绚烂绽放,就注定了下一秒的永远消逝,又像昙花。我们可以给生命打很多的比喻,但生命就是生命,那样的原汁原味,回味无穷,却让我们捉摸不透。
妈妈前些日子查出胃病,去了外婆家调养,我能做的难道不就是铭记她曾经的叮嘱,还有常打电话,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说几句贴心的暖心的话,铭记她快要到来的生日吗?我还能做其他的什么来捍卫这模糊而又柔弱的生命?
奶奶长叹了一声,像是终于抹掉了一些事,一些让她怀念感伤、一直放不下的事,像是一根心头的刺,拔掉了,就不痛了,但是神经也被麻痹了,没有悲喜,笑不出,也哭不出。
奶奶深邃的眼神朝我这边投来,却又穿过了我,射向遥不可及的天空中的重重云朵。我也朝那边望去。
那里面应该就是天堂吧。
“走吧。”
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回了目光。
我反过头看见稍带疑惑奶奶的神情,会意,黯神地握住她的手:“奶奶,我想起妈妈了。”
我看见奶奶的眼眶通红,却哭不出。
我眼睛也发热,却只勾出了一抹淡淡的笑。
看见
九天之上火花重重,在极为绚烂的烟花的空隙中,我看见了满面笑靥的妈妈。
大钟敲了十二下,我咧开嘴,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笑容,对着电脑视频里的她说,老妈,新年快乐啊!
奶奶看见了,幸福满足地笑着。
我不知道她是否已经明白,每个人都是在死亡的陪伴下生活着的,或者,她是在以笑的方式哭,以快乐的面容来把自己悲痛的心紧紧包裹起来,忍着一步一步脚尖上的透心的痛,再跟她往昔的好姐妹说了声,嗨,新年快乐,看看,他们都很幸福呢。
好想给奶奶一个温暖的怀抱,可是又不忍心拿自己的幸福去跟她炫耀,或者是假惺惺地陪着她痛哭。
“嘭——”
这是妈妈那边的声音。
外婆老屋是在一片原野上,附近只有寥寥几户人家,极为空旷,所以电脑那头的声音都是空远的。就好像在一个寂寥无人的山谷,在茂密阴翳的深林间,有一位仙人,坐在一块经他点化的仙石上,轻轻地闭上可以看透世俗的双眼,拂袖拿出一支萧,心深深沉淀在那个世界,吹出悠然的箫声,却又被一个误打误撞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撞见了。
我想象出,在那个悠远的原野上,朵朵烟花像第一次出门的精灵,欢呼着,惊奇又喜悦地蹿升至漆黑的天空。灿烂火光映照在妈妈脸上,我想,妈妈一定要把时光停留在这里,她以后要牵着爸爸和我的手在片原野上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地幸福下去,永远幸福下去。
怜
新年第二天听闻,官司继续。
邮箱:1183120237@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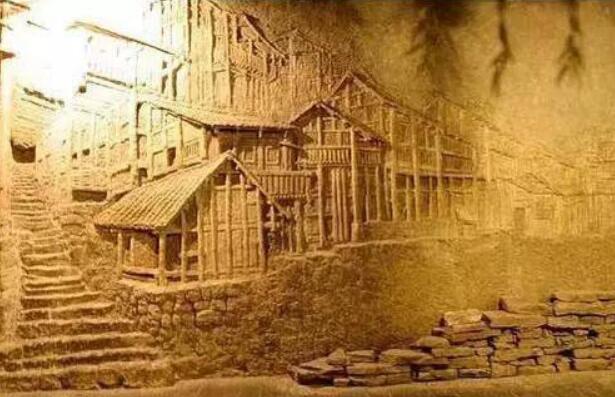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暗恋你的学生时代
暗恋你的学生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