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她咀嚼着这个字眼,常常被弄得支离破碎。她依然安静地坐在车座上,脸贴着父亲的后背。
夕阳开始下沉了,红彤彤的火球隐在了路旁白杨树的尽头,就像一个永远不可追求的梦,那么遥不可及。西天的残霞下是她的家乡——那个依旧贫穷、落后的小村庄。
“冰儿”,父亲沉默了很久,“不必太想家,有空写写信,或者打个电话到镇上的菜场里报个平安。”
“嗯”她轻轻应着,却费了很大力气,因为喉咙已经哽塞。她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哭”,她一遍遍对自己说,但是,泪,依旧模糊了她的视线,整个世界一片朦胧,那种令人窒息的“朦胧”。
夜色很深了,路旁的灯闪着寒光,夹杂着秋风,透骨的凉。父亲把她送到车站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了。
“冰儿,你呆着,别乱走,我先回去了。”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都深秋了,他还穿着那灰布外衣,脚上穿的还是母亲前年赶做的那双布鞋。他在家里就同女儿说好了,送她到车站,天亮了镇上的那位丘大叔会带她去城里打工。
父亲转身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头,“冰儿,不是爹不疼你,不问你,你都十七了,该懂事了” ,说完便走了。她听到父亲的声音多了些许哽咽,她只是站着,却不作声,看着父亲苍老的身影消失在夜暮中。
远去了父亲的脚步声,夜出奇地静,连虫子的声音都没有,铁冰想,大概它们也都去忙着准备冬眠了吧。
她小心冀冀地倚坐在墙角,望着路灯发呆,慢慢地又仿佛回到了过去。原本贫穷的家又多了个弟弟,从此她的童年便有些苦涩,连每星期吃个鸡蛋都成了奢望。父母很疼她,弟弟也很乖巧,但是她总是说她不需要太多东西,因为她懂得,她多吃一个鸡蛋,父母也许会因此饿上一顿。她很小就懂事了,人们总是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是一个很美的秋天,父亲卖了家里一头幼仔猪为她准备了学费,从此她有了新的生活。家里生活依旧清苦,但是铁冰学得很快乐,每一学期总会捧回一张奖状,这时她的嘴角会扬起了一丝笑意。风更凉了,钻进了她的衣领,她用手相互搓着,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搂在怀里。
她以为凭自己的聪明与勤奋会考上一所大学,然后成为一名作家,写村子,写学校,写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但是初三那年她辍学了,母亲得了不治之症,父亲为此借了不少钱再也没有能力供她读书了。她没有闹,一点都不难过的样子,因为她心疼父亲双鬓的银丝,她心疼弟弟冻得红通通的小手。她翻开书,惨淡灯光下依稀可见靡页上写着“英国查理王子曾经说过:责任是一种不可推御的负担。”这一直是她的信仰。
她在家两年,替父亲忙家务,照顾弟弟,过早的操劳使她那双本该和同龄人一样柔嫩的手变得粗糙、结实。但是这一切都还不够,这个秋天父亲终于答应让她出去闯一闯。于是她在这个地方、这个阴暗的车站,她轻轻地抽泣了起来,毕竟才十七岁,但是她一点都不怨恨父亲,她知道父亲回去还要喂鸡、喂猪,十岁的弟弟也许喝着冷稀粥,也许父亲还要熬夜去地里拔菜,也许他都顾不上合一下眼皮,又要骑车去镇上卖菜了,也许……
她不愿再推测下去,而其实这本是真实的生活,她不愿回忆起那苦涩与酸辛。她蜷在角落里,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但是她稚嫩的肩却不得不扛起一切,因为她终究要长大,终究要学会承担。
夜,依然静静的,只是多了她轻微的鼾声,她梦想着有一天能拿起笔来,但是她不知道还要多久。她想学夸父,但是她不是夸父,于是她只能承担,痛苦着,并且要幸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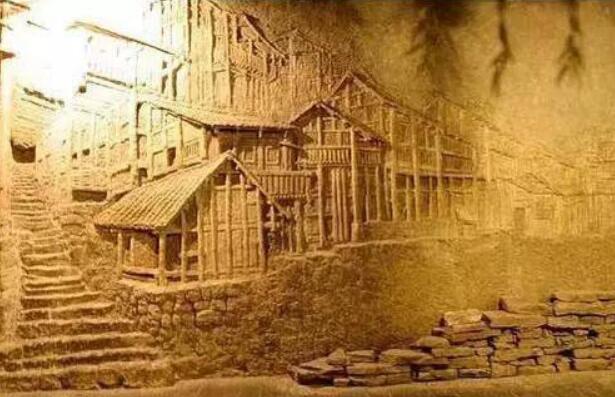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嗫?暁雲?
嗫?暁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