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十夜
年味消逝的差不多的深夜,我坐在电脑前,敲打一篇许久未曾动工的文章。
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一点文采,足够养活自己,却不必出名的人。我很喜欢一个朋友的说法,她说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作者,而非作家。人出了名以后,日子天翻地覆,我承受能力不高。写手没有名气,养不活自己。
为了成为一名成功的作者,我和祯若讨论过多次,祯若的意见我从来没有采纳过,却依然坚持不懈的与她讨论。祯若和我相熟的很不正常。她是我初中三年的同班同学,可惜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乎如同陌生人,后来我们毕业,后来我们变得很熟。
祯若理应和我不熟。她几乎就是我截然相反的一面。她痛恨自己的祖籍,我是爱国主义热血亲年;她是极端主义者,我一般不去自己惹麻烦;她在高档商店买淑女套装,跟我讨论韩国明星,我恨不得去地摊淘男装,喜欢枪战剧;她钟爱三文鱼,我看到就想吐;她喜欢狗,我喜欢猫;她比较矮,我比较高。
祯若问我的理想,我说考古,她说你脑子有洞?我说生化,她说你去死吧!我说我想当旅行作家,她说大学老师怎么样?
我以前写东西很有癖好,只用钢笔,墨水必须是蓝黑色,只写手稿,把字写得很端正。后来我一直没有稿费。
我的第一笔稿费是人民币100元,发表在一本教育类书刊上,至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发表的是哪篇文章。
有段时间我四处投稿,干很缺德的事情,一篇稿子发N次,于是也没有音讯。那段时间,我很有激情,整天梦想着稿费啊稿费,由稿费一路联想到学校小卖部里的烤香肠,当然编辑们不懂一个没有零花钱的学生对小卖部烤香肠的渴望。祯若更不懂,祯若对我一切装穷真穷叫穷的行动都趋之若鹜,一副懒得理你的样子。
凌晨
我很困,有一些黑眼圈,随随便便倾洒在眼角轮廓上的淡墨色。屋外在化雪,窗户很浑浊,墨绿色的老旧窗帘上有拇指一般大的洞。
站起来的时候腰肢闷痛,嗯哼着发出喃喃的干笑,回到房间觉得空气很差,附到桌前去开窗,铁窗框发出低哑的声音,我感到一股模糊的冷。从脚底传来。
我冲了热水袋,毫不留情的踩在上面。袜子是新换的,中午从抽屉里抽出时还套着塑料皮贴着标签,散发着格格不入的气息。
温和的没有抵抗力的温度贴在我的脚底,不情不愿。双脚依然冰冷,稍稍向上提一提,便能感到更清晰的冰冷,是黏稠的,让人害怕的。我把热水袋从双脚下解救出来,丢到一旁。
夜色漆黑,覆盖雪的颜色。白昼明艳,看得到漫天不规则的雪花飞舞。
我感到冷,手脚冰凉。我只穿了两件黑色的不厚的衣服。蹲在电脑面前,空调上罩着厚厚的布,漫无目的的打字。门外有一个男人睡在沙发上,呼噜声响亮、毫无规则,常常让我忘记打字的顺序和逻辑。因为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原因,我来到这个世界,他又出了一些力,把我养到这么一个颓废的年龄。
还有一个女人,睡在另一个房间,呼吸声安静,我带着耳机,放着Ineedadoctor,很难捕捉。
我不恨他们,他们说爱我。我无法失去他们。
我渴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种渴望超越了我想要去旅行。
旅行是我很少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件事。去西部,去云南,去北方,去俄罗斯,去冰岛、挪威,或者去非洲。哪里都可以,不报旅行团,托人帮我买张廉价机票,呆上一两天,然后离开。这种想法仓促而缺失周全,我丝毫不考虑签证与景点的问题。
祯若大概已经睡了,消息栏很安静,空挡、陌生、诡异、安全。
我捏着一只冰冷的面包,吮吸、咀嚼、吞咽。吃了过多食物以后,味蕾不再需求,神经重复着机械习惯的动作。我瞄了瞄茶几上52°的白酒,酒瓶是地中海蓝,诱惑、安静。酒精的刺激对于我尚有作用,所以我没有去触碰。曾经对咖啡味敏感,在一杯杯浓咖之后暗淡下来,我不想失去太多的敏感。
我想起了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小学四年级,不认识祯若,认识一些现在已经不记得的人,不懂很多现在不想懂的事。
那篇小说在当时觉得很血腥,名字叫地下室的冤魂,充满了年轻冲动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幼稚,原稿早已不见,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好搞笑。那是我写的唯一一篇传奇,现在只有故事,我自己只生活在故事里,传奇让我陌生。
读者除了我,还有乔那。
我在幼儿园和小学时代,有三个固定的在当时形影不离且唯一的朋友。一个走一个来,足以体现我喜新厌旧的积习和当时让人羡慕的幼稚。
乔那是第三个。当时她写了一篇关于精灵公主的和我交换着看。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失去联系,我过完空虚真切的初中三年,在网上查到她的学校,给她寄了张明信片,没有署名。
她认了出来,花了两天回信。
我关于小学同学后来的一些故事皆是从乔那那里听来。她小学毕业后去了直升的中学,小学的大部分同学后来都成为她的初中同学,初中是个已经可以保存在记忆里的年龄,我一直认为,乔那还记得我已经是个奇迹。
如今霸气的乔那,和略带荒唐的我,那个时候都是无与伦比的幼稚。
我的初中同学没有一个是小学同学,我有的时候庆幸,还好祯若没有再早一点认识我,不然我的事迹一定会被她当成课间闲谈和创造八卦的最佳材料。
霸气的姑娘乔那,她的话比较少。
十一晨
我压根不知道曰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叫我往稿纸上写:“古人曰”,我语言不加修饰的时代在班主任千言万语的教诲下学会习惯的在文章里加上比喻拟人夸张。
是不是所有人的曾经回忆起来都让自己觉得好笑。
祯若对回忆很在行,她会不动声色的告诉我她在好几年前的一个中午站在走廊里大声唱歌,走廊最门口的班里有人抬起头来瞄她,她于是就很放肆的笑。
祯若还回忆她视之珍宝的爱情。祯若喜欢的男生、毫无疑问和她的身高有很大的差距。祯若对她梦中情人展开强烈攻势的时候我并不在场,或者在做作业、要么听歌、要么纯粹在不上课的教室里大吵大闹,总之祯若失恋以后我出现了,成为最佳倾诉对象。我只见过那个男生的一张侧脸照,一张白净的瘦骨嶙峋的脸,上面打满了惊恐的表情、说啊啊啊我胖死了。我面无表情的看过、不打算发表任何评价。
祯若在爱情里毫无智商可言。我在没有爱情的世界里充满理智。所有追过我的人在我眼里不幸都成了笑话,至今为止我只失过一次手,这样的战绩我还算比较满意。
二年级的时候班里跑的最快的男生说非我不娶,我拉着乔那和他打了一架,居然赢了。四年级轮到成绩最差的一个男生天天给我带糖,后来因为我甩了他太多的巴掌他终于受不了痛苦而走,一群小学生为了此事八卦了整整一年。至今我还在上六年级的妹妹跟我信誓旦旦说起班里的八卦我就想起那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并忍不住打寒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小学时代打人从来都是用尽全力,好多年不打人以后我想起我年轻时手下的受害者,情不自禁为他们默哀,阿门,希望我不要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造成伤害。
初中过得很清静,连我妈都承认,我初中的确长挫了,丑姑娘没人要,脾气暴躁智商不高的丑姑娘更是没人要。我倒是享受清闲。
高中的时候碰到我的小学同学,半年以后开始追我,我把他送的东西当着最后一排所有人的面扔到垃圾桶,他不死心,托了他一有点娘娘腔的哥们来劝我。
他哥们和我原来关系不错,那件事后我彻底对这个娘娘腔的男人改变看法。
娘娘腔说,他真的很喜欢我。
我不喜欢他。
能给他一次机会吗?他睡着的时候还在说让你不要离开他。娘娘腔说酸话的功力比我强大的多。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能知道是谁么?
不能,滚蛋。
我没有骗人,我的确失手过一次。好在也只失手过一次,不至于让祯若笑掉大牙。喜欢上他以后,我很清楚的知道他一点也不喜欢我。我拒绝别人时的毫不留情让我清晰痛苦的预感到表白的后果。为了劝自己早点收拾包裹走人、刚开始几个月我写了很多关于痴情怨妇终遭抛弃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原型经常是自己活着祯若,现在想起来用我们两个神经质的性格作为怨妇的原版再合适不过,虽然祯若一定不会承认。
我在初恋之前一直疑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心动是一个很抽象的很具体的词,乔那的审美角度显然和我比较相似,而祯若和我几乎就完全相反。
祯若在很早的时候喜欢过自己班里的一个男生,当然只喜欢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段莫名其妙的感情在祯若遇到另一个男生之后被她自己迅速消灭干净。
那个男生,怎么说呢,是我的青梅竹马吧。
青梅竹马这个词在小说里是一件很浪漫的让人向往的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至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件灾难。
有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同龄男生和我一起长大,一个刚好比我大整整一百天,另一个比我小一个多月。祯若喜欢的是那个讨人厌的小弟弟。
不论是弟弟还是哥哥,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的我揍起人来从来不手软。从小被我揍过的人大都在升学和转学中消失。可是我的青梅竹马们很不幸一直无法消失。
每当我痛苦的回忆这些不堪入目的往事的时候,祯若就会很夸张的笑起来,笑的快要抽住,然后大声的说您老活该。
我的青梅竹马小时候被我扇怕了,在我面前从来不敢提及往事,可是他们的妈妈,把我骑在哥哥头上踹他屁股当做茶后最佳笑料,百笑不厌,每次聚餐后必提一提,从我干出这些荒唐事后一直笑到现在,笑了已经快十年。
我只能铁青着一张老脸靠在沙发上,我的青梅竹马不动声色的在一旁偷笑。的确如果他此时笑出声来,我一个肾上腺分泌过大就可能将旧事重演。
反正已经被笑了这么多年了。
十二夜
今天去了学校出黑板报,黑板报这个职责,我担任了十余年,业绩极差,可是每届班主任都死活不让我退休。
我在黑板报上潇潇洒洒写了一篇长文,外面在飘雪,第二教学楼还没有开课,学校切断了电源,我手机充不了电,还灌不了热水,手冻得像猪蹄。
祯若见到会很开心的。
祯若在家无所事事。
她和我聊天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两次语重心长的时候,不过大部分时间她都无所事事。我也一样,每天都要做很多很多的作业,做作业的时候当然是无所事事。
我曾有一段很幼稚的时光,那段时光我很执着,很向上。会写很励志的作文。后来大概被祯若带坏了。
初中老师告诉我多用些修辞,高中老师告诉我要突出真实感,大部分时候我会当做他们两个更年期发作吵个架,可是真正写作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纠结、作文云云,不是日记,更不是小说,我不能在上面写满他妈的今天老子忒不爽,我得拎着一纸清静上交作业。我读张爱玲,读白落梅,读安妮宝贝和饶雪漫。读张悦然,读韩寒,从来不看郭敬明。
我有很久没有往各大杂志编辑们的邮箱里投作文,最近的信件有些多,为小说出产的大幅减少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后来我学会在深夜对着电脑一个人絮絮叨叨说一些鬼话,让自己觉得自己说得很有哲理。写作文的时候,我小心翼翼的用着修辞,尽量不让自己被自己恶心到。这样纠结下来的作文拿给祯若看,她基本都是:你丫真矫情啊!
很久没有把小说拿给乔那看过,跟乔那之间没有电话、没有短信,加了QQ号但是从来不聊。我们保持传统只有通信。
乔那用蓝色0。38的水笔写白色的明信片,字相当潦草,远看挺潇洒,看实质内容的时候非常想哭。
祯若和我之间也通信、祯若的字写得比乔那还难看、不可远观不可近赏。看了祯若的来信我会很欣慰,觉得自己写给她的信她一定看的懂。
我有一只像素很低的手机,我强迫多很多人,逼他们看我用手机拍下来的字。居然没有人怪过我。我后来想了想因为我没有强迫过祯若,不然她会灭了我。
在很早写的一篇压箱底的小说里,我对祯若的形容是:你很小,但你很强大。
熬夜熬久了会成为习惯,不过昨天有个习惯熬夜的人告诉我他要早睡,他明天要早起去竞赛班上课。他跟我说晚安,我没有回。
他是我喜欢的男孩子,我在心里和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必须装出对你毫不在乎的样子。
乔那告诉我晚安的拼音有我爱你的意思,我承认我有些矫情,不过从此以后我弟弟和我说晚安我都回再见。
我突然想起来上个学期我被竞赛班踢了。老天作证,我真的只是去上着玩儿的。
夜不深,窗外很黑。
祯若说今天夜黑的很晚,我没有发现。对面那幢楼的等还几乎全部亮着,不过我打算睡觉了。在大晚上和我的电脑说了一些琐事,一些心事,不知道它听不听的懂。
世界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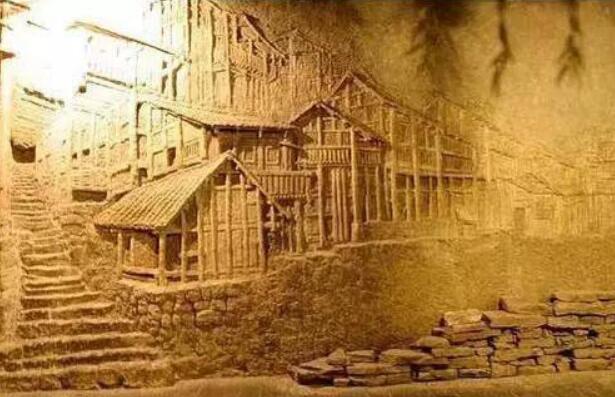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茵茵酱
茵茵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