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得了一种莫名的病,所以卧病在床的时候多,出远门问病求医的时候多,到大队的医院拿药打针的时候多。
卧床的日子,大人们都出工去了,孤独一人的我整天望着窗外明亮的世界,心里独自黯淡,巴望着有人背着我出去走走看看;上医院的时候,由于当时山里尚未通车,所以不管是路程远近,我都指望有人背上我,免除病中的我步行的艰辛。
我的这些愿望在很多的时候还总能实现。卧床的日子,只要出工的母亲回家了,就会背上我到村里村外到处转转。这时的母亲总会扶起我,然后蹲下身,成一尊优美的雕塑。我总会双手围住母亲白皙的颈脖,母亲反过双手托住我,然后站起身,迈着碎步,踩笑了那一路野花。母亲就这样颤悠悠的背着我,我的头就贴着母亲的背,吮吸着母亲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心,也因迷醉而发颤。
出远门求医的日子,大多是出过几次远门的二哥带着我。到公社、到区里,到县城,最远到过武汉。其中最难忘的还是那次到武汉去的情形:二哥背着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我,在县城火车站混上了火车,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心思体味第一次坐火车的快感,欣赏窗外世界满目的风景,我被来自体内的钻心的痛楚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巴不得早一点到医院,早一点解除我的病痛。终于到了武汉,可二哥可能是为了逃票,不敢通过验票口,背起我沿着火车来的方向,往回赶。铁路上的枕木被我数得记不清数了,可抬眼一望,路还是没有尽头,我只能听到伸长脖子的二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只能闻到二哥被汗水湿透的身子散发出的异味儿。我就在这上下的颠簸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长廊的长椅上,只见坐在地上的二哥已累得像一滩泥!
到大队医院拿药打针的日子,大多由在大队读书的二姐带我去。我家在山上,大队在山下,约有几里山路。二姐只比我大两岁,一般的时候,我是不要她背的,但有时病痛发作,她就会背上我,慢慢地走着,尽管我的双脚都快拖着地了,被驮着的我也不见得舒服,但看到与我个头差不多的二姐吃力而痛苦的神情时,我就会一言不发,老老实实趴着,心里总会生发出许多的愧疚。终于有一次,背着我的二姐在下山的时候,被一颗石头磕绊了一下,她踉踉跄跄着想平衡自己的身体,但最终还是没站稳,背着我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急忙努力地爬起来,骇然看见二姐的手上、脸上和额头上鲜血直流。二姐哭了起来,不知所措的我也跟着大哭起来,二姐就这样一路哭着,牵着同样哭着的我到了医院,而她自己只是把伤口处稍微处理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地赶着上学去了。多少年以后,二姐对我说:当时我只是怕你摔着了,要是那样的话,回去真不知怎么跟大人交待。听后不禁让我心热眼湿。
是啊!亲人们的背像一座坚实的大山,驮载着我童年的悲喜,也托举着我童年的希望。
多少年过去了,我渐渐长成了一棵虽不粗壮却也挺拔的树,也不用亲人们背着我去东往西了,更何况母亲的背因岁月的重负而变成了一张弓,一弯月,无法再负载我的痛苦和欢乐。但我始终不敢忘记,那痛苦的岁月,以及因我的痛苦而带给亲人们的苦楚。但我至今依然感念无限,有了这些经历,人的生命历程中,无不充溢着柔柔的温情和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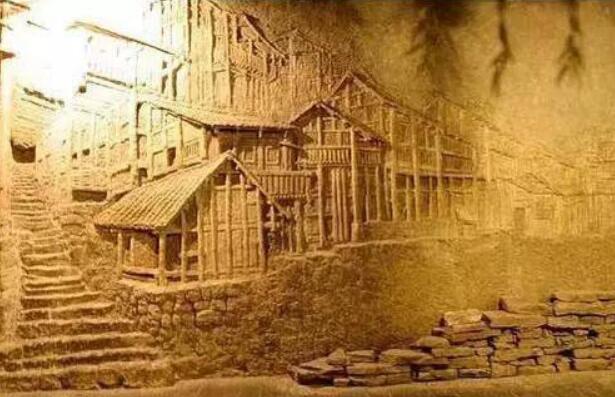



 loveJx宝宝
loveJx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