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余光中,则是他感人肺腑的《乡愁》,知是一个诗人,一个饱满浓浓情意的游子,渴望越过那湾浅浅的海湾。在识余光中,是那意味深长的《听听那冷雨》,冷雨顺着夏门街的幽幽巷子,一直淋漓到我的内心。
也正是那一季又一季的冷雨,敲打着那巷底绵绵思绪。他的心底苔藓有多厚?我不知,但厦门街的雨巷他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那狭长的巷子延伸,似乎不是从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可前尘隔海,只剩有再听听那冷雨,我想,不尽的冷雨淋透了一个游子的赤子之心。他是江南人,从金陵年少到川娃,再渡海,印证了那个年代的风波。
辗转五十年,半个世纪,才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地方,可年幼的记忆却迷失于现代,朦胧中却见沧桑巨变,从黑发少年到白发老者,不知要经历多少岁月的滑落,多少流水的印刻。那天,他怀着虔诚的心,一步又一步,一阶又一阶,登上中山陵,他感慨不已,他也只能感叹。“到乡翻似烂柯人”,更何况多少年来,萦绕在心头的记忆,虽然近在眼前,却似隔着前,却似隔着千水万水。想起他的诗,《与水草拔河》,他哪是在水草拔河,那分明是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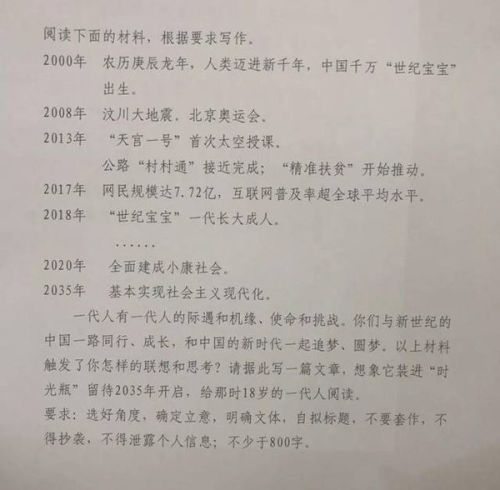
 再被注册打死你
再被注册打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