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我像一只被宠坏了的小猫,不捉老鼠反而胆大包天。
爸爸的脾气很暴躁,骂人的时候,他那两只快要鼓翻的眼珠不动的盯视着我们,还有恐吓的面孔,咆哮起来时像一只要吃人的饿老虎,全家人都很怕他,而我不怕他,却始终被他制服。
小时候的不懂事,没有空虚埋怨,知道玩就足够了。不懂得世间非非事事,心放得开,玩要玩得痛快。而忽略别另内之事,孔芳香之事而另其求其小。
那时候的爸爸是一个酒鬼,每一次出远门回来,总是醉的不堪,满身的酒味真难闻。跌跌撞撞地回来,便倒在地上,吐的满地都是。看着哪个不堪的场面,既恶心又伤心。
有些人喝醉酒,就会乱来。譬如:乱打家具啊、乱骂人啊等等。而爸爸醉了就会默默无言的睡了,可我很恨他,他不关心我们,对我们的学习或其它方面他不闻不问,我失望,失望没有得到父爱。
记得有一次,爸爸很晚都没有回来,我们全家人坐着一直等啊等,总是见不到他的影子。妈妈担心起来了,妈妈说:“你爸爸今晚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 都还不回来,会不会和谁去了”。我知道妈妈平时的时候和爸爸爱吵架,但这一刻,妈妈的言行举止证明了她的担心。我也忐忑不安,心总是跳个不停。左等右等, 爸爸还是没有回来,全家人只能默默地睡了。
半夜三更的时候,门终于被敲响了,是爸爸回来了,带着沉重的步伐走进屋,没有吃饭的睡了。
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们他踩到了迷魂草。他说:“他一直顺着路走,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分不清哪条是回家的路。于是,就乱走了一条,谁知,天公不 作美,让我走错了。越走越到不了家,原先一只很亮很亮的手电筒现以变成火红火红。走到一村苗寨里,一点不起眼的光惹得狗吠不停。后来,迷魂草散了,大脑清 醒过来。到一户人家去打听此地,啊!原来是走错了”。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爸爸深悟到了什么,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看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并非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少数人。
初一时,我得了一场病,脚突然而然的痛起来,越来越痛的厉害,甚至到了走不了路。爸爸带我到处去医疗,最终没有医好,医生说:恐怕要锯掉。听到 这个不信的消息,我对我真的失望了,真的感到无药可救了。-再后来,真的走不了路。疼的哪一只脚只要着地,就会加倍的疼,疼的哭喊不得。
妈妈很相信迷信,而爸爸从来不相信迷信。为了医好我的脚,他们什么都不顾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放过。
有时候在晚上,疼……疼的哭喊,爸爸和妈妈当时真的很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爸爸只好把我背往医院,医院离家约有三四里路,在加上我沉重的身子,爸爸加快脚步地飞往医院,爷爷空身赶往后面也没跟上。到医院时,爸爸满身大汗淋淋。他没有休息,忙去把医生叫来。
医生帮我输液,爷爷整夜没合眼的陪着我。白天的时候,爸爸因为上到班,所以,没有时间照顾我。
剩下的时间,只有爷爷和母亲照顾我。母亲虽然才三十八岁,但是,身子很弱。而爷爷已六十四岁了,身子也很弱,他们依然背着我跑了两三天。
后来,住院了。爷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又是几天过去了,手都被输液针刺得无数次,有些发肿,却始终不见效。
于是,爷爷和奶奶就带我去威宁照光,最终发现没有什么病。爷爷和奶奶都感到叹息:“怪了”,这一刻,我感到彻底地玩完了,难道非要废了我的一只褪吗?我在思考,思考我以后的人生。
回家后,大家都想尽办法的想办法。后来,褪肚儿坡越发肿大,还有点发青,便去医院开刀。虽然打起麻痹药,但是,我很害怕,害怕开刀后同样无奈, 不敢想,不敢看。我紧紧地抱住爷爷,爷爷说:“小情,没事的,别害怕,马上就会好了”。那一刻,我只听到刀子在我的褪上化了几下,那声音就像快刀斩乱麻一 样。“哗”地一声,血流了出来,那血红里带黑,难怪会如此的痛。手术完了,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舒服。我笑了,大家都笑了。
之后在医院住院输液,爷爷一直陪着我。还有很多关心我的人,他们买了很多很多补体的东西来看望我,我发现:我真的好开心。
出院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看望我,大家都这样问我:“小情,好了吧”。
我恢复了健康,家人终于放下了这个沉重的担子,都露出了笑脸。
爸爸的话很少,他的一句话在我心中是鼎千言万语。从初中到高中,他开始关心我们的学习,不怕累,不怕苦的赚钱来给我们几兄妹读书。
而我似乎是家中最特殊的一员,对我,他们很有信心,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我,希望我能考个好的大学。
以前我总是抱怨爸妈不关心我,现在,我明白了。原来,父爱不表现在语言上,而是通过许多事情来表明;而母爱则表现在语言上和某些事情上。
而父爱是默默地;
母爱是积极地;
则沉默并不是死寂,无言并不代表无心。
一句话,一份情,永无回味。
原来爱一直在我身边周旋,而我却不知道。
爱无处不有,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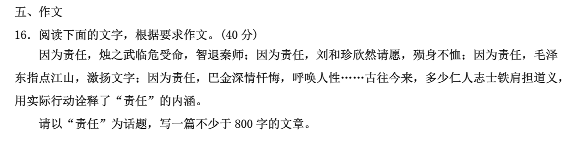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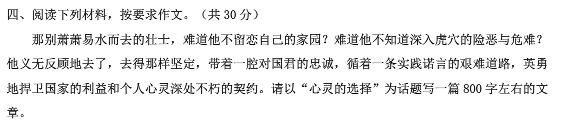
 間单
間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