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余晖消失在北方大地上,华灯初上的城市徐徐拉开帷幕。妈妈在医院的手术室外看着暮色四合的城市,那张脸上挂着一如既的往不动声色的表情。
两个小时前妈妈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像是一纸诏书,我们赶到医院。医生简单的交代签字,外婆被推进了手术台。外婆病的太唐突。
病情比想象中的严重,大概是她常年的病痛我们一直没有发现罢了。
妈妈与外婆一直有着无法化解的恩怨。这是怎样的怨怼我始终无从知晓,时光流逝,我用不太敏感的神经发现其实长久以来,关于矛盾,唯一没有释然的人只有母亲而已。
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一人怀着愧疚的心情独自居住,离我家只有20分钟的车程,可每次过节只有我和爸爸去看望她,妈妈在心里视她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我记忆力,她从未喊过外婆一声“母亲”。
依稀记得小时候外婆总会给我买不同颜色的小金鱼,放在透明精致的小鱼缸里,还放进去几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外婆不会敲门,只是默默的放在门口,再孑然一人的默默离开。次日早上我小心翼翼的把鱼缸放在窗台。等回到家里。它已经安静的躺在垃圾桶里。从始至终我不曾看到门外的愁容沧桑的面庞,也没有勇气去想象。现在面前的一扇门,上面挂着“手术中”的字样,刺眼的像是召唤死神的信号。
城市陷入黑暗的漩涡,昏黄的路灯亮起。妈妈蜷缩在冰冷的座椅上,时间粘稠的流逝,上一秒容光焕发的在电脑旁敲敲打打的她,瞬间的憔悴了,面无表情的隐藏了内心的风起云涌,佯装坚强。那惝恍的眼神流露了她内心的忐忑。静谧走廊中暗淡的灯光掩藏母亲婆娑的泪眼。我一直认为妈妈不会为外婆流一滴眼泪,这十几年对外婆淡漠的如同外人,温暖的亲情像是在浩瀚海面上流浪,居无定所。
这个夜晚漫长而阒静,我与近在咫尺的妈妈像是相隔两个世界中。母亲一动不动的凝望着窗外,无法直视那扇门,像是站牌。我想毋庸思忖我就可以懂得她此时此刻的心情。终于放下了倔强的桎梏。她不愿看到刚刚登上路途的幸福与释然转瞬驶向终点站。
外婆在那个叫幸福的站牌下孤独的等待了多年,这个夜晚,母亲亦将抵达。
这样的夜漫长的可以把一个人吞噬掉。彩虹灯奄奄一息,24点之前一切都将成为历史。这些眼泪肆无忌惮的留下来。像是母亲的祷告。她一直爱外婆,一直都是的。那些往事还给天使。
滴答…滴答…
十二小时后外婆从麻醉中清醒,母亲俯身在她耳边呢喃道:妈,病好了,咱们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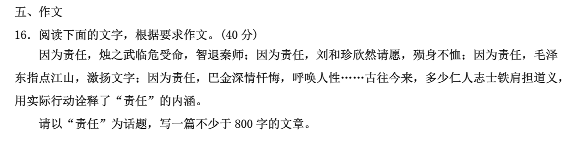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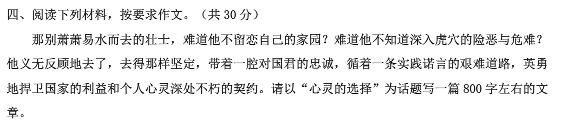
 就是这么骚_
就是这么骚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