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凌晨,我从还开着的窗外看到了一架闪着光亮的飞机,一下一下的,从暗黑的天边明亮的轰轰地飞过。我知道,这个晚上我就注定要失眠了。于是,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电脑,怕会突然忘记些什么一样。我想我必须要写些什么。
在那天,我就这样,亲手把自己的梦给葬了。或者说,把自己活埋了。
我还在,还在这个我迫切想要逃离的地方。这里已经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什么了,自从那栋楼推动以后,就把这里永远地贴上了悲伤的标签。所以,在这里,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快乐的,只有难过,和无时不刻的难受。
看着他们一个个收拾光东西离开,甚至争先恐后地跑着离开...让我一个人越来越孤独。
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他们过了中考,要离开。
他们都要逃到快乐的天堂去了,是吗?只有我还守着地域么?
我本来以为可以离开这个悲伤的地方,然后没心没肺地去忘记这里。
可是,我还是没能离开。够可悲的。
当班主任叫我别去铭选的时候,我没有坚持,只是不假思索地吐出还算清晰的几个字。哦,划掉。然后看到那两条粗线条在上面划过的铺天盖地。只剩下那个让我感到有点作呕的地方,我后三年里面的唯一归属。我已经没有什么权利选择了,我只能一遍遍地嘲笑自己的懦弱。
我终是这么的不确定。
那么,我只能坐在原地看着,把头埋在膝盖里哭泣。我还必须在这片荒芜里继续庸俗下去。这就意味着紧接着的另三年的隐忍。
而他们都坚持到了中考的最后一场考试后……有几个人问过我为什么要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没话说了。不是我自己先放弃的么?呵呵。
夏天的阳光比任何时候明媚,只是照也照不亮心底。这个时候,它就是无济于事的。
我不甘心地又去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三年,很长。于是,我就真的认为三年很长很长了……
一年一世纪。
……
三年三世纪。
我想,以后。我会更加地冷漠,每天背着那从未减轻过的沉重书包,更加面无表情地从许多人身边安静地走过,再也不会主动去打招呼。我知道,我必须一个人适应一个人的孤单,不需要再去附和任何人。我必须伪装得再好些,伪装得没有一点儿空隙,那样我就就还是会快乐的。一个人尽管会很累,但不再像和那么多人扯上关系的那么累了。
我害怕三年之后,我又再发现我没有了这三年的回忆了。就像没有了前两年回忆一样。那时候,这样的失去,会让我疯狂么?还是,那时候的我,已经学会麻木了。已经不带任何感情的每天做着练习,整天埋下头记满整本书的笔记。拿到很好的成绩,拿给别人看。看,这是我考的。我安慰自己说,那样子谁都会快乐的,身边的人会快乐。他们快乐,我就会满足了,即使我并不快乐。
我发觉了我已经离不开文字了,我不知道高一的那年,我该怎样选择。我是会义无反顾地填上文科,还是会又像活埋一样把自己埋在理科里,埋在那些厚厚的数学参考书,烦人的物理公式?最近在看郭敬明的第一本书《爱与痛的边缘》,他说理科就像我的右手,文科就像我的左手。砍掉左手还是砍掉右手?左手还是右手?左手?右手?他们说文科前途光明,但脚下,没有路。
突然为人们感到可悲,活着只是为了追逐那些名利,一直都是。很累。我怕到时候也要被卷进去了,跟他们一起去抢夺。读书也是,是一种追寻名利的手段,这是我一直讨厌读书的理由之一。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他不想为了名利。
我越扯越远了。但我想我现在应该想得更远些,我怕以后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就没时间了。
这样算起来,我的一生。似乎只有15年的时间让我感受到彻底幸福。而其它时候,只能任别人摆布了。被世界丢弃。
从昨天开始,没有理由地喜欢上摇滚。可以听到脑袋轰鸣,听到脑子整个乱了,却依然舍不得关掉它们。这是一种麻痹的仪式,让你在麻痹里找到知觉,哪怕只是一点点。我把音响开到了中上级,让整张桌子都在震动。就像小四说的,可以听摇滚听到死。
戴夫·哈克说摇滚使人沉溺于其中而麻木不仁,懒散不堪并脱离实际。
前两天看了两部关于摇滚的电影,摇滚夏令营、Raise Your Voice,看到那些张扬的青春,就疯狂地喜欢上了摇滚。
最近听Linkin Park,喜欢他们用嘶吼到嘶哑的声音喊出的音乐。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但我能找到一种共鸣。像他们把他们的那首Intheend用很多版本唱出来,却都只是想要表达同一种感受。上网的时候,从摇滚贴吧里看到一张摇滚专辑封面,我忘记它的名字是什么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封面上的那个人用刀片在自己的手臂上,割出一串鲜血渗透出的字母,还有刀片上存留下的最后一滴血液。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液晶屏幕上反射出的我,带着诡异的笑容。
你懂么?
如果太害怕,闭上眼就好。
原来,我也能抛开写那些像诗一样短的文字,写出很长很长的一篇,比那三年还长的文字。我想在那三年里我可以做到。原来,我还能像我非常崇拜的数学老师说的那样,我还有好多的潜能等待着开发。就像我现在,话多得讲不完。现在已经很晚了,肚子又空了,胃又在痛了。所以,胃是不能无聊的,必须有东西让它消化。否则,它就疯狂的痛着。忧伤也是,要有快乐的养分给它。
那就写到这里,因为没力气了。睡着就不会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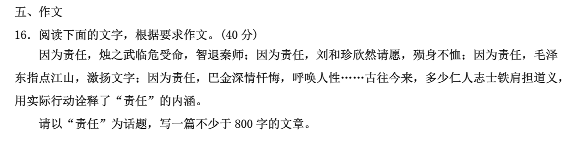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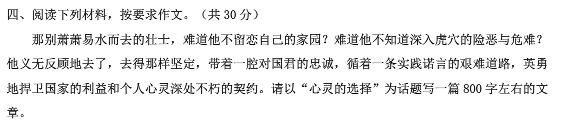
 凉城不暖少男心
凉城不暖少男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