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惫侵占我的眼睛,眼皮闭合着,渐渐堕落在一个梦里。在梦里,我变成一只全身黑白色毛,棕色瞳孔的眼睛的小狗。
走进森林,交错的树枝把阳光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调皮的我踩着阳光,一蹦一跳,小脚掌踏在湿润的的泥土,冰凉冰凉的。我顺着阳光走,走着走着,遇到一个巨大的荆棘丛,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便抬头看,哇,好高呀!于是,我透过缝隙,看见有一间小木屋,紧闭的玻璃窗,拉拢的窗帘,合上的木门。木屋旁有被日晒雨淋的摧残的旧秋千。房屋前中间有铺满石子的小路,两旁是杂生的野花。
煞是有趣,于是我努力用两个爪子挖呀挖,然后拼命从荆棘丛下钻过去,背上还挂着些小刺。跑到门前,吠了几声,没动静,便跳到窗台,欲图打开,可惜呀我这狗爪子啊,这根本是扒窗嘛!怎么开啊?里面的人似乎听到声音,窗帘悄悄地被拉开,一双和我一样颜色的眼睛露出,那煞白的小手拧开窗锁,慢慢往上推上窗门,我嗅了嗅他的手,也趁机钻进去了。
映着阳光,阳光给他轮廓镀上毛茸茸的边,这是个小男孩,病态的皮肤,忧郁的眼神,紧闭的嘴唇。他倚在窗边,静静看着外面景色,可惜没到几分钟,他不得不用手臂捂住双眼,赶紧拉拢窗帘。阳光好像刺痛了他,就像顽皮的小孩去逗弄那乱舞的火焰,最后留下锥心的疼痛。这孩子呀……得了一种病呀,不能见日光啊!
黑漆漆的屋子,只有那被阳光照射的窗帘所映出暗淡的光。这小男孩在这黑暗里待了很久,很久。没有阳光,没有朋友,没有父母,只有一身的病在缠绕着他。寂寞、病痛是他每天的食粮。眼泪早已流干,那心啊,流血了,愈合了,麻木了。
突然间,一只小东西就这么闯进他的黑色世界,它那单纯得没有杂质的小眼睛,一下子掳获了他的心,他的小鼻子碰到他的手,湿润而温热的气息。他心里泛起点点涟漪,小小的快乐在他心里一点一点地萌芽。
当男孩的手飞过来,我本能地惊慌地躲避,逃到桌底下。我仅仅听到小小的叹气,他静静坐在桌前椅子,稍微还听到刻刀和木板相撞的声音。桌下的我,屈着前爪,托着头,等待着,瞧瞧有什么动静。才过了一小时,耐不住寂寞的我,走到男孩脚,用舌头舔着他的脚指头。他也停下手头活,蹲下去,抚摸着我的头,揉顺着我的毛发。当我一抬头,鼻子撞上他的小手,我还是高兴地伸舌头舔着。男孩竟然咧开嘴笑,眼角泛起快乐的鱼尾纹,也许是手心痒吧……
我喜欢在屋子乱窜,喜欢乱吠,而小男孩却从来不恼,或许对于他说是千金难求吧!有时我也静静伏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阳光,小男孩就会有莫名的失落感,他抚摸着我的头,扁起嘴,问:“小东西,你想要离开呀?”唔——唔——我只能压着声带,担心地看着他。他松开手,不自觉地苦笑,自嘲道:“我是不是太傻了,竟然问一只不会说话的东西……”轻轻地摇头,不在说话了。
我很想去安慰他,不过我不能说话,或者是这样的问题,我无法用是与否来回答。你不傻,可是多愁善感的你,总让我担心;你很傻,可是你坚韧地活到现在。我只能做的,用舌头舔舔你的手,愿温热的呼吸能安慰你,从手心到心田。
梦将持续不了几分钟了,一切都渐渐变模糊了。当我睁开眼时,阳光依旧明媚,依旧不变的格局。趁着记忆还没消退,再次闭上眼,默默祈祷,对上帝说:“能否把我那温暖的阳光分一半给我梦中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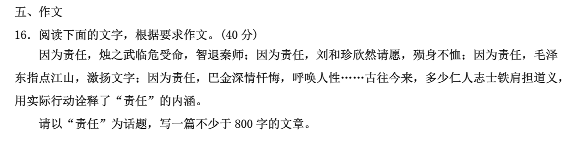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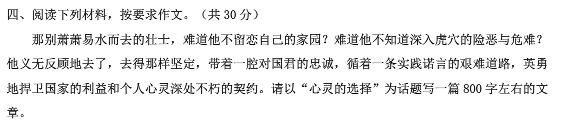
 小先生2830310
小先生283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