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现代性》读书笔记2500字:
除了要改进我们要继承的或先赋的禀赋、资源、魄力、意志和决心中的缺点外,我们还要永无止境地改进和自我改进。并且不管人们制造的是什么东西,人们都可毁灭它。成为现代,等于意味着——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无法停止下来,甚至于更加不能保持静止状态。我们发展并注定要保持发展,这与其说是因为“满足的延迟”(delay of gratification),还不如说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因为永远满足的不可能,满意的范围、努力的终点线和让人平静下来自我祝贺的时间,要比跑的最快的人运动得还快。满足永远是未来的事情,实现、完成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失去了在他们取得成功之时感觉满意的可能性,然而,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成为现代。意味着永远居于人先,意味着处于一种持续的侵犯状态(用尼采的话话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成为或者至少努力去成为一个超人,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成为现代还意味着,拥有“只有作为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才能存在”的特性。就这些方面而论,这与我们的祖辈们的境况没有多大的差别。
有两个特点使我们的境遇——我们的现代性的形态——与众不同。第一点是早期现代错误观念的逐渐瓦解和迅速衰落,即相信沿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会有一个终点,有一个我们可以达到的终极目的,一个明天、明年或者下一个千年就要达到的完美状态,一个某种形态的良好社会。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现代化任务和义务的解除控制和私人化。不要回头看,也不要抬头看;看看内心深处的你,那里,才是你自己的智慧、意志和力量——这些都是生活改善所要求的工具——应该的栖息之所。

再也没有伟大的领袖会告诉你去做什么,告诉你如何做,才能使你从所作所为的后果中摆脱责任;在这个个体的世界,只存在其他的个体,从他们身上,你可以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事务,并为你对他们的例子的信任而不是为其他的东西去承受完全的责任。
把它的成员看做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商标”。然而,这种对待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它是一个每天都要上演的行动。现代社会存在于它的持续不断的“个体化”(individualizing)的行动中,就正如个体的行为存在于对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相互卷入的——网络的每天重新塑造和重新谈判中。这两个角色没有一个能长久地保持固定不动。因而,“个体化”的内涵也在变动,永远体现出新的形态——正如过去历史累积的结果逐渐削弱它承继下来的规则一样,它也在制定着新的行为规范,并为游戏永远准备新的赌注。“个体化”现在有着与它在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含义,并且和它在现代时期的早期——这个时代被赞扬为人从严密编织的、共同依附的、监控和强制实行的组织里解放出来的时代——传递出来的意义也截然不同。
简括地说,“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identity)从“承受者”(given)到“责任者”(task)的转型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副作用)负责。换句话说,个体化存在于自治——根据法律上权利——的建立之中,而不是事实上的自治是否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
因为这些,人类不再凭他们“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正如萨特极好地指出的: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并不够——他还必须像资本家那样生活(注意,前现代时期的王公、爵士、农奴或者市民未必一定如此,而且也不能这样说那些穷人或富人出身的人)。定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也只是现代生活的特征(而不是现代个体化的特征,这种表述明显累赘;提到个体化和现代性,就是为了证明一个同样的社会状况)。现代性用强制性的社会地位的自主代替了他主。对“个体化”而言,这在整个现代时代——在它的所有时期和社会的所有方面——都是有效的和适用的。然而,在这个共同处境中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像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行动者的类别不同一样,它也使持续的几代人与众不同。
早期现代性的脱域是为了重新嵌入。脱域是社会认可的结果,而重新嵌入却是摆在个体前面的任务。一旦僵化的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那么摆在现代时期早期的男人和女人们前面的“自我认定”的任务,就意味着一种“过名副其实的生活的”挑战(赶上时髦,向左邻右舍看齐),与正在形成的被阶层限制的社会类型和行为模式保持一致,模仿他们,遵循这种生活模式,适应这个阶层的文化,不要掉队,也不要违背它的规则。作为承继而来的社会归属的“家庭出身”,已经为虚构成员资格的“社会阶层”的目标所代替。前者是一个归属的问题,而后者(成员资格)却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成就标准;与家庭出身不同,社会阶层必须是加入进去的,而且成员必须连续地在一天一天的行为中更新、再确认并得到检验。
古典现代性中的个体在因家庭等级秩序瓦解而脱域出来后,在疯狂寻求“重新嵌入”的过程中,利用他们新的权力和新的自治机构中的头衔。而且不存在接纳他们的“床位”的短缺问题。阶层和性别是自然的客观事实,大多数个体遗留的自我独断任务,就是通过像其他的位置占有者所做的那样去适应确定给自己的位置。
阶层不是固化了,而是固化越老越难了。稍不小心,就滑落了或下消失了。准确的说,这就是使得往昔的个体化与它在风险社会时期,在“反思的现代性”或者“第二现代性”(贝克不止一次地用它来指称当今时代)时期里采用的形态区别开来的东西。没有给“重新嵌入”提供“床位”,而且这些被寻求的、可能是先决条件的床位,证明是易损坏的。且常常在“重新嵌入”的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突然消失了。那里有相当多不同尺寸和不同风格的、数量和位置都在变化的“音乐椅子”,这使得男人们和女人们不断移动,没有“完成”的希望,没有休息,没有“成功”的快意,没有可以使人打消疑虑、停止担忧而放松地达到目的的满足感。在被“脱域了”的个体所走的路(现在路是要长期走下去的)的尽头,见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
向每一个人再次保证,独自与困难作斗争也是其他所有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而且再次砥砺低落的士气,振作萎靡的继续斗争的决心亦是如此。那群受害者能给予的唯一帮助是,关于如何从自己的无可改变的孤寂中生存下来的建议,以及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着需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和抗争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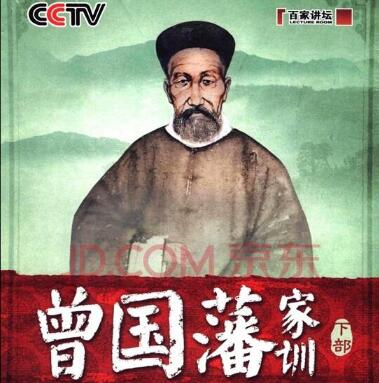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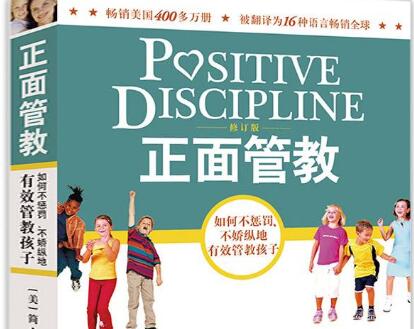

 烟草味道37627847
烟草味道37627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