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完了《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村上Radio》,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大桥步画的插画。
三不五时地哭一哭(在没人看见的地方,被窝里最好,厕所还是免了),可以缓解内心的压力,对心理健康也大有好处。这条理论我很早以前看过,忘了在哪,从没确认过文献出处,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杜撰,尽管如此,还是下意识地选择相信,或说是我希望相信,悲伤也能带来些什么,闪着冰冷光辉的好东西。
戏剧性地在人前掉下眼泪,指望别人来安慰。这种事情你干过吗?
倒不是想评价什么——慢着,说出这句话的我难道不是正在进行“评价”这个行为吗?
如果是在石器时代,置身下一秒说不定会从哪儿蹦出一只剑齿虎来的野外,还能想哭就哭的人,一定对“此刻身边有人可以依赖”这一点确信无疑。
说来奇怪,我看个电影都能跟关不掉的水龙头似的哗啦啦猛倒一通眼泪,哭得感同身受,两个眼圈又红又肿。
生活里遇到的几次事情,每次让我喉头一股想哭的情绪直往上翻涌,却眼眶干涩,半滴滋润一下眼睛的泪水都憋不出来。
像连接两端的通道被从中切断了,或者存储泪液的水库枯竭了。好端端的怎么会枯竭呢,可能是水库这家伙晒太阳,太舒服所以晒过头了。想也是,金色的暖融融的日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一幅充满了希望的图景,明亮而丰盛的光线常常让人产生错觉,变成那种会傻不颠颠地龇牙笑,由衷地说出“天底下没有坏事情,再糟糕都有解决之道。”这种虚张声势的乐观台词的人。
然而天色渐渐暗下去,那股激情渐渐衰退,滤镜魔法失效了。再一看那水面(暗绿色,混浊看不见底),漂浮着的只有三三两两的昆虫尸体。

村上说他不会在随笔里说别人坏话,不会写自夸和自我辩解的话,也不会写和时事政治有关的话题。这是他写随笔的原则,我觉得一个作家写这种东西,颇类似一个杀手在接活儿的酒馆里酷酷地吐出烟圈,对新来的中间人仔细讲解说:“我当杀手呢,一不杀女人和小孩,二不杀钢琴家,三不杀会勾手四周跳的花滑选手。”
不说别人坏话很好理解(但并不一定理解得对),在我想来,我们对别人的认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偏颇的,偏听偏信了一面之词,或是因为某个阴差阳错的误会,给一个人安上了他没犯过的罪名,还是写在会被很多人看到的地方,哪天发现了真相(当初竟然是错怪了他么?!),怕是要懊悔到以头抢地的程度,关键还没法抹消这影响,就算是再次在公开平台上发声说当初是误会,又怎么保证当年看到过那番污蔑言论的人,这次也能恰好看到这篇澄清的文章呢?期间因为那番不实言论,对当事人造成的困扰,又该从哪里下手去“弥补”?
自夸挺好避免,反而是“自我辩解”经常注意不到,有时无意识就开始解释起自己的行为来。一切行为的背后都有当事人能够逻辑自洽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都要像破案那样,把原因也一起告诉大家知道、寻求体谅的。
说出原因,有时像在教堂里对着看不见面孔的神父做了次无比虔诚的忏悔,转眼走出教堂就把那层沉重的罪恶感抖落在身后,毫无负担地再犯一次。
单纯依靠“辩解”,并不能得救。
时事政治……如果改变不了,保持缄默,吗?
可能就在一片令人愉悦的沉默中,任何改变的希望都被封死了。
生气的时候,想一想“我在生气”,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生气”,用理性的思考而非一时冲动来判断一下,这个理由值不值得。
说来简单,写下来也简单,做起来真难。激烈冲突中往往任凭“生物本能”占了上风,等理性好不容易回归,面对的只有一摊被怒火摧毁得看不出原样的废墟。
再过一会儿,“后悔”就要来了。它总是会来,当理性还在。
我没有“肯定能起效”的办法,最近在尝试的是,尽可能让理智在线,把“生物本能”拼命往意识深处压,让它昏昏沉睡。就算真遇到了什么争执场合,它想浮上意识的表层兴风作浪,刚醒过来一会会儿,还迷瞪着,比较好压制。
记住我们是人,而大多数怒火是不必要的意气之争,褪去“人”的光亮外皮,打回龇牙咧嘴、眼球布满血丝的野兽原形,为了滑稽的奖励彼此拉扯撕咬。
真羡慕啊,温柔的人,无论面对什么境况,都能轻声细语把事情解决的人。
一直是人。作者:雁行凛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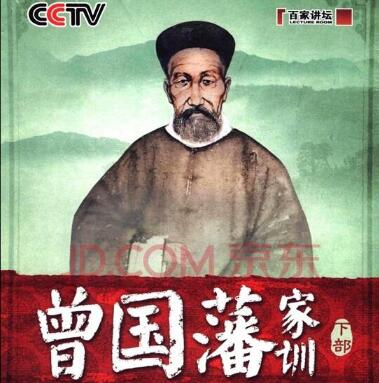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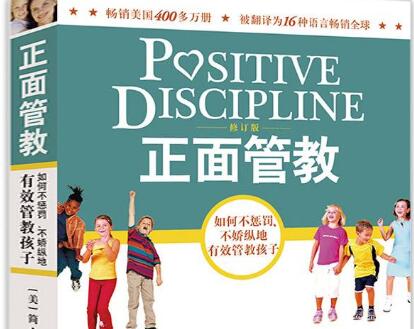

 苦逼逗逼二逼
苦逼逗逼二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