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nǎi nɑi,狭义上是父亲的母亲或父亲的母亲的姐妹,广义上是年龄较大或辈份较长(至少两辈)的女性
感恩奶奶的散文
那天中午,快到吃饭时侯,还不见你下来我就上去叫你。
谁料想,这一顿饭你永远吃不上了,空着肚子走了。
这几年你都跟我在佛山漂宿寄居,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带着年近九旬的你每一次找出租屋都碰很多灰,屋主都不肯将自己的老屋租给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安身。是我苦了你。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总是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你的孙子是穷人中的一个,不能给你置房子,让你在大暑的前一夜暴死在10平方的出租屋里的一张小木床上。他一生都将愧疚于你。你走的那么突兀,连临别的话也来不及说上一句,勾魂鬼也太不厚道了。他一生都将冥想你最后那一句想说什么。
连喊带哭,大哭,恸哭,确认了你再也不能回应我。你的魂已走了很远很远,再也,听不到。
驼了廿五年的身板终于直了一次。你仰天而睡,嘴张着,空着一肚子的话射向天花板抵砺的孤灯,你干瘪的乳房露着,已经干硬状,太酷热的天气你昨宿只能裸睡,桌上的旧风扇有气无力的摇着头。这个国家的这个孤苦老人,你的身体因远遁而变得更轻,更轻。我却无力为你完好的穿上衣服,所有的关节都僵硬了你。我面对冰冷的尸居然也有怯怕。倒是与你偶有绊嘴的孙媳妇利索的帮你着上左手衣袖。再翻动你瘦小的右肩,转动你单薄的身躯,慢慢的给你的遗体穿好衣装。多么心碎,看着你如此不甘心的僵硬的面容,全无牙齿的嘴皮还撑开着,临走前你该有多少话儿要说。你是中暑走的,床单上挣扎着一滩未干的盐沫一般的汗渍,而我至少来迟了四个小时。满屋子夹杂着尸臭的空气在深深责怪我。三十三年的祖孙的缘份就此揖别。从此,你倒是可以不用再跟我挨苦受罪了,我却不能再赡养你,你养了我二十多年,我却才养了你十年,多么不公平啊!
你膝下无儿无女,我则自幼无父无母,幸得有你,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并供我读书。你六十岁才开始领养我,真不容易,奶奶,我成人了,却不能和你一摸一样,勤勤恳恳、朴朴素素、一尘不染,你宽宥了我一切的坏习惯与懒惰,以三倍于母亲的年纪和慈爱着你这个小孙娃。我的白发苍苍的奶奶。在我十七岁那年,我再不忍你以七十五岁的高龄再挣钱供我上学,我下狠心缀学了。但你又不给我南下打工,我呆在家就发疯似的写起诗。那时,县的广播电台也发疯似的天天播出我的作品,乡邻听到的都在你面前竖着大拇指说你的孙子天才啊,甭说你有多乐了。后来,报刊也频频出现我名字,你大字不识一个,却也拿着报纸仔细地瞅,有时拿翻了看我也不忍说破。少年得志却亦耽误了我的青春,囚在家里写了几年的文,钱银却无甚收入,家里的经济一度紧张。之后,更为落魄的我曾在县城的大街卖画,卖字,长长的头发飞扬在路人异样的目光中像划破世俗那么刺眼。终于在家呆不下了。古人言,父母在,不远游。我却在你八十岁那一年离家出走,把你一个人留在家。出来的那一天除了车票我手上只攥着皱巴巴的四十七块钱,而你手上也不够一百了,还得挨到第二个月我发工资才能寄钱回去。日子,咋就这么难,出来的几年,我看守的铺头一再失窃被盗,工资都被扣在这些铺头资金了,每月都是借钱给你汇回去。对于刚出来月工资400元的我每个月只能给你寄干巴巴的100块钱,而你则省得一年下来还有500块,看着那藏在墙缝用旧报纸包得发霉的钱,我不敢想象奶奶的日子是如何过的。想想,这些年我们夫妻儿仨的食用近两千还过那么紧凑,再想想奶奶十年前几十块的伙食费(那年头物价也差不多呢),心酸不禁。出来打工,就剩奶奶一个人在家,饿了一个人烧饭,病了一个人看医生,寂寞了一个人自言自语,奶奶是生是死,我可以说完全不知情,打电话奶奶耳聋,写信奶奶又不识字,心憋得难极了。过年才难得回一次,两个互相牵挂的’人一年就靠这几天来治疗己经寸断的肝肠了。记得,第一年回去的那次,你硬是要挤在我床和我睡,我没有不适,我轻抚着你满是皱纹的额头,泪浸眼角,润湿耳根。于坚说他母亲是纯棉的母亲,100%的棉,他的意思就是他母亲俗不可耐的温暖、柔软、包裹着……落后于时代的料子,总是为儿子们,怕冷怕热。我则想说我的奶奶是纯麻的,奶奶给我的爱,像麻绳,虽粗糙却牢固,像麻袋一般装着稻谷一般的我,甚至像密麻的蚊帐包围着我,而麻烦,却留给自己。七八年后,终于熬出了头,我这个穷小子也讨了老婆,生了娃,把你接到身边,安乐的日子还没过上,没想到……你却……这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看着你被殡仪馆的人卷在布袋里被抬走佝偻成一团的样子,痛,有裂帛之力。这一别,是永远了,我想你只能凭记忆,一个剧痛的远方停在那里,你——远游的你再也不能回来。
次日,我和太太到殡仪馆办理后事。令我更痛的是我买不起棺木给你,寿衣和骨灰盅也是廉价的,在这个城市,连死也是讲价钱的。有钱的置个棺木也上万,没钱的像你的孙子给你只有一个纸棺,我很愧疚很痛。看着你被冷藏了一天的遗容,看着你那曾经深陷在你眼窝的,那苍白眼睑覆着你对我这三十三年来所有的几千丈深的溺爱,我几乎崩溃了。整个仪式都有工作人员安排着,想多看几分秒也被控制着,在最后时刻我的泪眼是怎么也看不够的。只有你,再不能睁眼。一夜薄霜敷脸,这世界已设任何新奇之处让你动容,唇嘴紧抿,鼻息紧锁,你再也不用着紧这个致命又多变的世界。我恸然用食指轻触一下你的冷唇,多么想再次靠近你,挨近你,亲近你,听你说。以至于,我听不到工作人员的断喝。在这紧要关头最后共存的时刻,就是分岔的肇始,你缓缓被推走被带走被永远收走。尽头由此展开,骨头由此脆响。目送着你遗体入炉,我在焚炉外抢天呼地的嚎哭不休,我太太在旁也泪旁满面,但与近旁一炉几十人集体合哭相比,这个世界留给你的场面实在太凄凉了。
你在火化机经历了平板炉近半小时的火化,剔肉成烟剔骨成灰。出炉后你以髑髅相见,看着你仰躺的形状没有一丝肉的脱架的一堆骨头,白得刺眼,余炽后碎骨还有点儿刺鼻,你一块一块躺在那里,你一根一根与我分离,这是一种我们婆孙俩最后的面对,这是我们相处以来最后最无奈的沉默,你空洞洞的颅骨、深陷的颅中窝还是那么慈祥的望着我,没了皱纹的额骨那么光滑,聋了多年的耳朵终于让颞骨打通,面颅骨还是写满了和蔼,而上颌骨和下颌骨我是多么希望它此刻发出声音来,平时在电视看到让人毛骨悚然的髑髅骨头,此刻我是多么的留恋而看不够似的。
奶奶,骨头中的奶奶,那细碎的和大块的骨头,留给我最后的奶奶的样子,我伏跪着看旁边的工作人员把奶奶的样子一点点拆散,还要把奶奶的骨头一根一根被敲碎,那一堆骸骨,奶奶,是你留给我最后的敲打乐,是最后的碎,你的形体最后只留一盅灰粉。我将骨灰盅拥在怀里连罐带你也不够五斤了,或者说去罐的重量你已轻不足斤,我却捧得手沉如铅。最后将你的骨灰盅放进一个纸箱内,包装好,掩人耳目,将你通过客车运回故乡。在这个城市,我买不起墓地给你。叶落归根,是我给你最后的最体面的伪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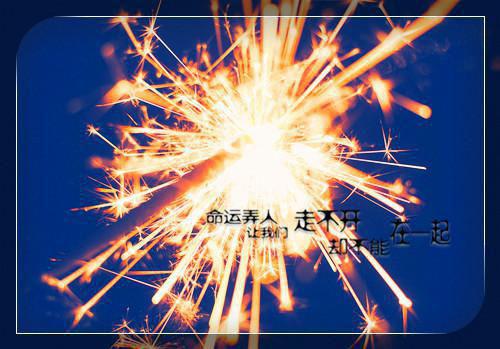







 想嗦不能嗦不能嗦又想嗦
想嗦不能嗦不能嗦又想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