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7年。
寒冬。
燕的世界,已是白雪一片。
太子丹派出的刺客大约已然抵达秦国了吧?燕的存亡,就只看这最后一博了。上策可要挟秦王悉数归还侵我的国土,下策可刺杀秦王,使朝廷闹乱,我燕国可缓兵临城下之急,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好计啊……
作为燕的士兵,我遥望秦的军队――连绵不断,阵形整齐,那深黑中泛青的青铜盔甲似与天相接,那一杆杆沉重的戈正直指我们的城池,楚、魏、赵、韩四国已成刀下之鬼,今唯存的,只有山东被破百余城的齐,以及这被刀架在脖子上残存的可怜燕国了。五六年的戎马生涯,多少个枕戈待旦的黎明,我深谙:无论你的武艺如何高超,指挥如何得力,不认清当下形式单凭一己之力,是万不能力挽狂澜的。军营中几个弟兄,因大势所趋,已然投秦。我擦拭着手中心爱的戈,它已久未沾血,从前的寒光闪闪仿佛不再,投秦吗?不,忠诚是一个士兵的本色,我断不能因了秦强我弱而背弃这精髓的定则。我的心慢慢坚定起来。
不久,荆柯失败的消息传到燕京。我震惊了,之前所有的计划都以作泡影,燕国的命运不知如何?背水一战吗?抑或是乞降?可悲的是,貌似圣明的大王选择了后者,并且杀死了太子丹,于是我由震惊转为愤怒,这就是我忠于的大王吗?不,我恶狠狠地对自己说,“这是愚忠!”于是在一个满月之夜,我打点包裹,负着戈,转投秦营。临行,我用匕首划破手臂,用绝望的血液在惨白的墙壁上题下:
祭血诗
残月渐已圆,
锈戈今依旧。
号角喑然寂,
却终弃一战。
斯燕乞秦降,
祭血必自亡!
他日,我守卫在秦的宫门前,看见大王带着礼物,跪倒在秦王脚下,卑躬屈膝之态尽显,我,在心底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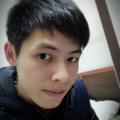 吓倒三千军
吓倒三千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