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一开头,用了这样一个,谬诞莫明的词,我知道,一定有人懂它。
他是这样说的:
“当一个刚刚来到世界上,就如亚当和夏娃刚刚走出伊甸园,这时他知道什么是国界吗?知道什么是民族吗?知道什么是东、西方文化吗?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孤独,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渴望表达——不管他动不动笔,这应该就是,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写作,曾经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现在仍当从这里出发,而不是从政治、经济和传统出发,甚至也不是从文学出发。这就是写作的零度吧?”
我愿意把零度肤浅地解释为:共鸣。
只是从碰触中,一点一点察觉到的生命的意识,只是跌撞里,对世界发现中的欣然与恐惧。于是从心底流露出一种渴望,对着天空,对着树林,对着大地上跃跳的生灵,轻轻地想要表达,或是想记载生命的启迪,或是渴望冲破肉身与环境的限制。
写作,不知多久时就与等级,画上了兄弟的符号。记得儿时那些珍贵的老师的笑颜,觉得那里便是我写作的意义。哪一个哲人说,人生就是从清晰的执着,变得觉得看什么都不是。后来,社会的功利化的学说一点一点侵蚀到我们孩子身边,我感到惶恐无力后便是寻找生活的意义。年少的轻总要先为心灵,寻找特殊的重,读书,然后寻找,我越寻找,就越焦灼,觉得这世界上还没有适合自己的人生定义,可以我是如此想看清自己脚下的路,感到越来越沉重的背负,渴求着生命真正的释放……
你说年轻时读书在寻找什么,他们说,共鸣,呵呵,那我和他的零度就在了。
他说:“在逻辑的盲区,或人智的绝境,勿期圆满。但你的问,是你的路。你的问,是有限扑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尼采有诗:‘自从我放弃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
而史铁生的意思是;自从我学会了寻找,我就已经找到。
我找到了什么。零度,是一种冷峻,一种坦然。
史铁生说,有人说他很乐观,他却觉得自己偏偏是最不乐观的那一个。这很有意思,他说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得不写,好像有种力量让他不停地想自己的苦难,这大概是“第一推动”或者“绝对的开端”,只能是你与生俱来的悲观,躲不开也逃不脱的思索。你想着想着,就出来了。
我很渴望和他谈话。有人问我懂不懂,嗯,这又是什么问题呢,不是全部当然,你对谁的思考又能彻底了悟呢,我只是感到并不苦涩,而且,并不虚幻。
我起初也只是歆慕于他的文采,可是,这并不足以支撑我对他的爱,甚至信任,千里遥遥。多久我彻底感觉他的辞藻不重要,成了思想的一套表情。他成了唯一和我畅想在一个世界,他愿意和我分享愿意与我促膝交谈,我就常注视他一那睿智的眼睛,注视,只有关于爱的温然,或者,面对苦难的那张带笑的面容。我常常感受不到那些文学作品绮丽别致的气息,感受不到和他纸的距离。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的零度,我越想越模糊了。我只是觉得,那些引经据典,像是从经济、政治出发,类似数典忘祖,指从某种传统出发,则近乎原地踏步,文学的初衷原是在那永不息止的生命的探索中找到心魂的位置,在苦难中大喊“上帝保佑”后认识一个新的神——精神,写作本身并无法代替寻找,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真正地审视与反省自己,文学就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他无法向科学那样通向简单,通向人类如何强大,而是通向人类的苦难,那里有关怜悯,有关爱,有关友谊与祈祷,而那,也许才是人类复杂性真实的存在,“文学料必在文学之外,论文料必在论文之外,神命料必在神命之外,人的根性料必在现实之外。”
我背过他一些很经典的话,我尝试写了关于他的日记,我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那样,坚定不移的人,如此愿意听我的问题,如此平静了我的幻诞。我本来想借这篇文章议一议他的写作零度,可我想,算了吧,夏娃走出伊甸园,正是与世界有了灵魂的触碰,才有了他内心那些文字。我与史铁生,暂时还只是心灵的沟通,至于文字的切磋,思想的融合,怕是待以后我知识的增加了。
我又想到儿时写作的意义,老师的笑,这是真的,而且我如今若还这么想着,我也不害怕笔再写下去。
我是不是渐渐把一些东西看模糊了。还是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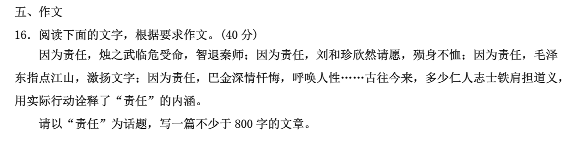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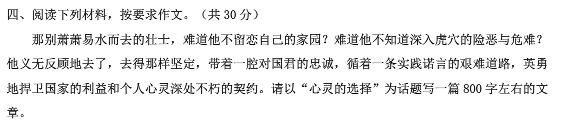
 达?矢抾哆拉?
达?矢抾哆拉?

